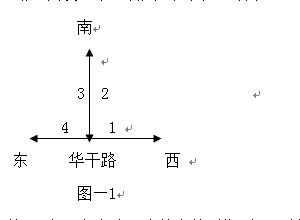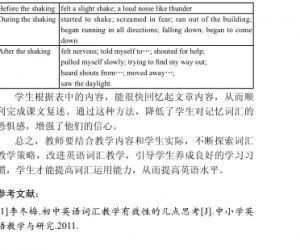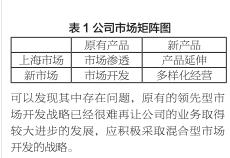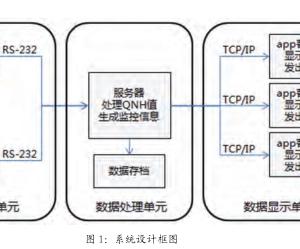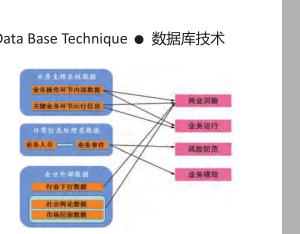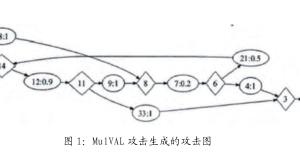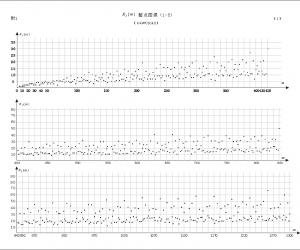客观的处罚条件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发布者:松原芳博著 王昭武译
热度0票 浏览158次
时间:2011年2月22日 10:12
关键词: 客观的处罚条件;犯罪论体系;结果无价值;行为无价值;责任主义;可罚的违法性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内容提要: 日本通说承认客观的处罚条件这一概念,认为其属于无关犯罪成立与否的情况。但是,这切断了犯罪与刑罚要件及其效果之间的联系,有违“犯罪是可罚的行为”这一定义。而且,这种将犯罪从刑罚考量中割离出去的做法,有导致犯罪论的形骸化之虞。事实上,作为发生可罚性程度之危险的介入情况,客观的处罚条件理应还原至作为可罚的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应该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与客观的处罚条件之间的相互联动,由此而导致了法律所应防止的可罚性违法事态的发生。基于这种理解,在行为当时,必须存在将来发生客观的处罚条件的可能性、行为与客观的处罚条件之间的相互联动提高了危险性、对将来发生客观的处罚条件具有预见性。据此,偶然责任得以排除,从而担保了责任主义。
一、问题之所在
日本刑法通说承认,某些情况虽属于实体刑法上的刑罚要件,但并不隶属于“犯罪”概念,并称之为客观的处罚条件[1]。例如,事前受贿罪中的“就任公务员” (刑法第197条第2项[2])、破产诈骗罪中的“开始破产程序的决定的确定”(破产法第265条[3])[4],等等[5]。在通说看来,将要成为公务员的个人只要收受了财物,即成立事前受贿罪,在其正式就任公务员之前,只不过是特别地保留处罚而已。然而,就个人收受财物而言,只要该人尚未正式就任公务员,就不会成为刑罚的处罚对象,即便起诉也是“无罪”,然而,却将此行为评价为“犯罪”,这无疑有违“所谓犯罪,是指能被科处刑罚的行为”这一定义,且切断了犯罪与刑罚要件、效果之间的联系。将要就任公务员的个人收受财物,这一行为究竟是否已具有可罚性程度的违法性,这本身便尚存疑问;若具备了这种违法性,在其就任公务员之前,又为何要保留处罚呢?这一点也不明确。将客观的处罚条件的存在理由满足于单纯的“政策性理由”,不得不说,这无疑是放弃了刑法理论的本来使命。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对此,有观点提出,应将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作为将行为的违法性提高到可罚程度的要素,还原至作为可罚的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6]。但是,此观点就必须回答:与行为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后事实,何以可左右对犯罪行为的违法性评价呢?而且,按照责任主义的要求,应对违法性的基础事实存在故意,然而,认为行为人对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存在故意,这是否合适,也值得探讨。
二、客观的处罚条件与犯罪论
1.犯罪的成立要件与客观的处罚条件
犯罪,是指该当于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说对客观的处罚条件是作消极的定义,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不属于犯罪的成立要件。本节想就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与各个犯罪成立要件之间的关系作些研究,以探讨这些事实是否真的不能属于犯罪成立要件。这同时也意味着,是从反面验证犯罪论体系。
2.构成要件与客观的处罚条件
构成要件首先承担着担保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性机能”,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属于刑罚法规所规定的刑罚要件,理应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对象,这一点应无异议。因而,不待“就任公务员”,便处以事前受贿罪,这不能被允许;由“就任公务员”类推,对担任公共性很高的非公务员职务者也处以事前受贿罪,这就与禁止类推原则相抵触。另外,作为有罪判决理由中必须明示的“应罪事实”(刑事诉讼法第335条),“构成要件”也发挥了刑事诉讼法的机能,事实上,也有判例将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包含在“应罪事实”之内[7]。这样,在具有保障机能与刑事诉讼法机能方面,没有理由将客观的处罚条件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强调构成要件的保障机能的贝林格,尽管在其早期的理论中,将客观的处罚条件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8],但在其晚年的理论中,却认为这些事实属于可将可罚性行为个别化、类型化的,能担保罪刑法定原则的“犯罪类型”要素[9]。
通说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乃至违法有责类型。为此,仅就与违法性的关系而言,构成要件将该罚则所预定的违法事实予以类型化。从这种违法类型化机能来看,构成要件不包括与犯罪的违法性无关的事实。通说将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这一点可能也是其理由之一。对于客观的处罚条件与违法性的关系问题,参见后述。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立足于责任主义,若对该当于构成要件的事实并无认识(或认容),则不能认定具有故意责任。如此,在划定故意的认识对象这一意义上,构成要件具有故意规制机能。但通说认为,不需要对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存在认识(或认容)。也就是,通说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作为不包含在故意的认识对象之内的事实,而将其置于与构成要件要素相对应的位置。然而,为了不以故意为必要,作为便宜之法,而将客观的处罚条件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结论的结论,更让人怀疑这不过是一种伪装,其目的正在于掩盖其本身对责任主义的违反。对于客观的处罚条件与责任的关系问题,参见后述。
3.违法性与客观的处罚条件
通说可能因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是行为之后的外部情况,而将这些事实作为与行为的规范评价无关的情况,从违法性,以至从作为违法性的类型化的构成要件中排除出去。这种理解的背景就在于,针对违法性的实质所采取的规范违反说(行为无价值论)。因为,在规范违反说看来,作为事后的外部情况的客观的处罚条件,与以作用于行为人的意思(意思决定机能)为使命的行为规范毫无关系。围绕“结果”的体系性地位的论争[10]鲜明地反映了规范违反说与客观的处罚条件之间的关系,因而,这里就规范论与结果的体系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做些探讨。
一元的人的不法论通过贯彻规范违反说,将犯罪的“结果”从违法概念中排除出去,使之成为一种客观的处罚条件[11]。一元的人的违法论认为,法规范只有作为命令、禁止作用于人的意思之时,才发挥规制机能,因此,法规范应以反映到行为人主观的现实为前提,不仅无法涉及脱离行为人的手之后的事态即“结果”,让受偶然的情况所左右的“结果”的发生影响到违法,更是有违责任主义。
但是,这种对不法的主观把握以及排除“结果”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夺违法概念的现实性、社会性根基,不得不说,这有违应以社会外界实际发生的事实作为根据的行为主义(Tatprinzip)。而且,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从违法(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中排除出去,也与实定法不相吻合,也就是,实定法中的很多犯罪,是否可罚、可罚程度均取决于结果如何。对此,一元的人的违法论认为,发生的“结果”属于客观的处罚条件,具有证明行为的违法性的机能。但是,行为的违法性才是处罚的根据,若承认这一点,就必须证明行为的违法性已经达到超过合理怀疑的程度,不允许通过“结果”的证明来取而代之。另外,在存在处罚未遂犯规定的犯罪中,原本毋需等到“结果”的发生就能证明行为的违法,并且,由于证明机能本身并不包括决定刑罚轻重的内容,从证明机能也难以说明未遂减轻。如果以可证明未遂情况下的不法程度很低为理由,而减轻其刑,这无非是承认嫌疑刑罚。由此可见,一元的人的不法论并不能说明,刑法为何要规定“结果”的发生。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日本的规范违反说(行为无价值论)的主流立足于二元的人的违法论[12],认为违法评价对象包括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但是,这种观点与作为规范违法说之前提的规范理论却并不协调。规范违反说认为,违法是对具有作用于行为人的意思并控制其行动的机能即行为规范的违反,那么,违法判断就必须是事前判断,不应为行为之后所发生的结果所左右;而且,行为不法以行为规范为内容,结果不法以法益侵害为内容,二者之间并无共通的指导原理,二者在对象、标准、根据等方面均具有不同性质,包含这些不同性质的要素在内的“违法性”概念已扩散到难以对其做出积极性定义。因此,二元的人的不法论也没能在理论上成功地说明“结果”的体系性地位。
为此,要给予形成犯罪的事实性、社会性之根基的“结果”以正当的体系性地位,在违法论上,就不能以作用于行为人意思的命令规范,而只能以否定不恰当事态的评价规范作为其前提,应该采取法益侵害说(结果无价值论),以惹起法益的侵害或危险作为违法性的实质内容。佐伯千仞博士是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还原至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的先驱,正如博士立足于法益侵害说这一点所表明的那样,可以说,这种法益侵害的观点可以提供一种契机,也就是,如同“结果”那样,可以使事前受贿罪中的“担任公务员”等事实与违法产生关联。笔者也是从此方向出发,尝试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还原至违法,这留待后述。
4.责任与客观的处罚条件
通说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本身并非责任要素,这自不待言,就是在不能成为故意的对象这一意义上,也与责任无关。
与通说相反,也有观点主张,应将客观的处罚条件本身作为责任要素还原于犯罪论。该观点从预防目的这一刑事政策的视点重组责任概念,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作为确保刑事政策上的处罚妥当性的事实,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属于纳入了这种刑事政策性考虑的“责任”要素[13]。的确,责任概念与预防目的并不完全对立,也有包含现实的刑事政策性考虑的余地,但是,“责任”概念若包含所有的政策性考虑,就将丧失其内容本身的限定性,也会动摇具有分析性的犯罪论体系。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属于客观的、外部的事态,它所承担的“政策性考虑”未必与行为人的“责任”具有亲和性。
是否需要客观的处罚条件与故意,在与责任主义的关系上成为问题。通过将客观的处罚条件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而认为不需要对此存在认识,这会遭到质疑:是否对责任主义的脱逃与背离呢[14]?对此,通说(处罚限制事由说)作了如下说明: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是对即便没有该事实也具有当罚性的行为予以特别处罚限制的情况,因而,即便没有对该事实的认识(或认容),处罚该行为也并不违反责任主义。也就是说,客观的处罚条件并非是给当罚性奠定基础的要素,而是对已具有当罚性的行为给予要罚性,因而故意不及于此亦可。但是,“限制”处罚与“奠定基础”只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而已,不可能在内容上绝对区分当罚性与要罚性。在这一点上,笔者也抱有怀疑:处罚限制事由说给客观的处罚条件附加故意不及于此这一大前提,这难道不是为了让其结论与责任主义相互调和的“循环论证”而已吗?
另一方面,站在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还原于违法(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的立场,就必须回答:究竟是坚持对客观的处罚条件不需要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将其作为责任主义的例外来说明[15],还是认为至少需要对此存在过失(预见可能性),或者是原则上需要故意(预见)呢?
另外,诸如携带酒气驾驶罪(《道路交通法》第117条之4第2项)那样,可以用具体数值来划定处罚范围的事实,在与是否需要存在认识的关系上,也属于客观的处罚条件,这一点留待后述。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三、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还原至违法(私见[16])
正如前述,法益侵害说认为,以法益侵害或危险为内容的“结果”是违法(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这意味着违法性事后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正如一元的人的不法论所指出的那样,结果发生与否取决于行为后的外部情况。在结果犯中,违法性会事后发生变化,既然对此持肯定态度,那么,对于包含客观的处罚条件的犯罪,也没有理由否定违法性的事后变化。在此观点看来,一般情况下,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作为将行为所产生的法益的侵害或危险提升到可罚性高度、发生达到法所预定的可罚程度的违法事态即违法结果的中介事实,可将其理解为作为可罚的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将要就任公务员者就将来将要担任的职务收受财物,即便发生了危及公务的公正以及对公务的公正的信赖的危险,但该危险当下仍止于潜在状态,只有当该人实际上就任公务员,从而发生“公务员处于不正当利益的影响之下”这一事态,针对公务的公正及其信赖的危险才会显现出来,才能达到可罚的违法性的程度。“公务员处于不正当利益的影响之下”这一事态并非客体的有形变更,因而在法条的规定形式上,与通常的结果犯有所不同;但它属于以行为为原因之一而产生的与法益相关的事实状态,可认为是(事前)受贿罪中的“结果”。“就任公务员”,这无非是将为发生这种结果而不可或缺的中介事实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予以类型化。
即便是通常的结果犯,利用与行为并无因果关系的外部中介事实而使结果发生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例如,试图杀X,将其绑在铁轨上,X被过往的列车轧死。尽管列车通过这一中介事实是发生死亡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但列车通过这一事实非行为人所能左右,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然而,在将这种预见可能的外部情况作为条件加以利用,而使结果得以发生的场合,只要能认定结果与行为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该结果就归属于行为。不用说,在杀人犯的场合,发生结果并非总需要存在这种中介事实,而且,可以用客体的有形改变来显示结果,因而不能认为这种中介事实属于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与此相反,在事前受贿罪中,一方面,对于发生针对公务员的公正或者对公务员的公正的信赖的达到可罚程度的危险而言,“就任公务员”这一事实就属于不可或缺的事实;另一方面,对这种危险的发生,也难以作确切的描述,因而,通过将“就任公务员”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而描述了可罚的违法事态。至于为何要规定“就任公务员”这一条件,除了是考虑到与这种法益之间的关系之外,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认为“就任公务员”是客观的处罚条件,与违法无关,这种通说观点也未能就作此要求的具体“政策性理由”做出具体说明。若认为在单纯受贿罪(刑法第197条第1项)等犯罪中,“公务员”身份是为法益侵害性奠定基础的构成要件要素,那么,也应认为事前受贿罪中的 “就任公务员”的性质与此并无不同。
笔者的上述观点不时遭到误解,被认为是要求行为者的行为与“就任公务员”等客观的处罚条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而批判笔者的结论并不妥当。但要说明的是,笔者的观点在于:要求行为者的行为与“针对公务的公正或者对公务的公正的信赖的达到可罚程度的危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任公务员”只不过是介入该因果过程的外部条件[17]。
这样,将“就任公务员”作为为了产生针对公务的可罚性危险的事实,而将其还原至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在解释论上就会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行为人收受钱财的时点,必须客观上可以预见到,自己会担任作为请托对象的公务员。按照相当因果关系说,若结果发生所必要的外部客观介入情况属于不能预见,所发生的结果就不能归属于行为。在介入情况属于缺乏客观预见可能性这种程度的异常情况时,就可否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事前受贿罪中的“就任公务员”,其本身尽管与行为并无因果关系,但若在行为的时点,这属于客观预见可能,则收受财物这一行为的作用,与“就任公务员”这一事实的作用相互联动所引起的“针对公务的达到可罚性程度的危险”就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
第二,必须认定存在这样一种关系:收受财物这一行为与“就任公务员”具体协动联动,从而发生了“针对公务的达到可罚性程度的危险”。也就是说,必须存在通过“就任公务员”而使得收受财物这一行为所引发的潜在危险已经显现出来这种关系[18]。为此,作为请托对象的公务与现实担任的公务必须在一般职权的范围内,属于同一公务。而且,在担任公务员的时点,收受财物的效果必须仍在持续。换言之,收受财物之后经过了极长时间、行贿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已经死去、行贿人等相关人员已撤回请托或者已丧失了利害关系之后,再担任公务员的,就不能认定存在因担任公务员而提高了针对公务的危险这一关系,应否定成立事前受贿罪。相反,将“就任公务员”从事前受贿罪的违法内容中割离出去,认为在收受财物的时点已经具备作为该罪的可罚的违法性,按照这种通说的观点,就不可能通过要求该行为与“就任公务员”之间存在协动关系而限定处罚范围。
第三,行为人在收受财物的时点,至少应未必地预见到自己将来会担任作为请托对象的公务员。按照责任主义的要求,要认定行为人具有故意责任,行为人至少必须对该犯罪的违法基础事实存在认识或预见,由于“就任公务员”是成立法所预定的违法事态所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事实,因而,在缺少这种认识或预见时,因对本罪所预定的法益侵害·危险化并不具有认识或预见,就应否定行为人存在故意。就客观的处罚条件而言,要求行为人对此存在认识或预见,这并不现实,前面已探讨了这一前提。但是,就事前受贿罪中的“就任公务员”而言,通常都是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却仍然收受财物,难以想象有对此并无预见者。这是因为,刑法第197条第2项所规定的“将要成为公务员者”,实际上就是指已预见到自己“就任公务员”者,若对“就任公务员”并无预见,也无法理解“将要担任的职务”、“请托”、“贿赂”这些用语的含义。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对破产犯罪中的“开始破产程序的决定的确定”而言—尽管就是否应以此为条件,在立法论上仍有探讨的余地—上述论述也基本适用。
四、以数值划定的要素
从是否故意的对象这一角度,在是否客观的处罚条件这一点上引起争议的,是诸如年龄、浓度、时间、速度等刑罚法规上以数值形式规定的要素。
刑法第176条后段、177条后段规定,对未满13周岁者(不以暴行、胁迫为手段)实施猥亵行为、奸淫行为的,处以强制猥亵罪、强奸罪。这里的问题在于,是否需要认识到对方“未满13周岁”?“未满13周岁”这一事实类型性地描述了该对象没有性的自由决定能力,正是为法益侵害性奠定基础的事实,因而属于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应认为其包含在故意的对象之内。而且,通过外观、口吻、行为方式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判断对方的年龄,因而要求行为人对此存在认识,也并非不现实。
《儿童福利法》将“儿童”定义为“未满18岁周岁者”(第4条),第34条第1项禁止对“儿童”实施法条所规定的特定行为,而且,第34条第1款第4项、第4款之3、第5项禁止对“未满15周岁的儿童”实施法条所规定的特定行为,第60条规定对违反这些禁止规定者科以刑罚。该法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第60条第4款规定,“使用儿童者,不得以不知儿童的年龄为由免除前三条的处罚。但无过失的不在此限”。对此可理解为,承认“未满18周岁”、“未满15周岁”是为行为的违法性奠定基础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使用者”以外的其他人,要求其对此存在认识;对“使用者”科以年龄确认义务,既处罚违反这种确认义务的过失行为,又将该过失的举证责任转嫁至被告人一方。该规定将针对使用者以外的其他人的故意犯与针对使用者的部分过失犯并列在一起,且转换了过失的举证责任,这些是否妥当,尚有探讨的余地,但可以说,该法律是将年龄规定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来对待的[19]。在将“儿童”同样定义为“未满18周岁者”的基础上,处罚那些针对“儿童”实施法条所规定的特定行为(第 4、5、6、7、8条)的《儿童色情法》也规定,“使用儿童者,不得以不知儿童的年龄为由,免除自第5条开始至前条为止所规定的处罚。但无过失的不在此限。”
另外,《有关确保汽车的保管场所等的法律》第11条第2款第2项规定,禁止“汽车在夜间(自日落至日出的时间段)在道路同一场所持续停车8小时以上”,该法第17条第2款第2项规定对违反者科以罚金。最高裁平成15年(2003年)11月21日第2小法庭决定(刑集57卷10号1043页)在认定本罪旨趣在于处罚故意犯的基础上,判定“要成立本罪故意,行为人在停车开始时或者其后,至少必须对超过法定限制时间的持续停车状态存在未必的认识”。由此可以认为,这里的“8小时以上”这一时间要素是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来对待的[20][21]。
《道路交通法》第22条规定,禁止以超过道路标示所指定的最高限速或者政令所规定的最高限速(《道路交通法施行令》第11条规定,汽车在一般道路上的最高时速为60公里)的速度行驶,以该法第118条第 1款第1项(故意犯)与第11条第2款(过失犯)处罚。本罪的故意或过失,只能是就行驶速度这一点而言,从118条分别规定故意犯与过失犯来看,第1款第 1项之罪要求对超过时速60公里存在认识,第2款之罪要求对此存在认识可能性。由此也可理解为,“超过时速60公里”这一要素是构成要件要素而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其次,《道路交通法》第117条之2第1号、第2号规定,就携带酒气驾驶而言,对“含有政令所规定的程度以上的酒精”者予以处罚,《道路交通法施行令》第 44条之3规定其程度为“1毫升血液内含有0.3毫克,或者呼气1升含有0.15毫克”。考虑到会类型性地有碍于安全驾驶,因而规定了该酒精浓度,这应属于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22]。相反,有力观点认为,将该数值包含在故意的对象之内并不合适,应将政令所规定的酒精浓度理解为客观的处罚条件 [23]。但是,将划定行为的可罚的违法性的事实理解为客观的处罚条件,这并不妥当。就行为人的故意而言,对于在驾校接受过培训的驾驶人,理应知道,若饮一定量的酒,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就会超过0.3毫克,要求对此存在未必的故意也并非不现实,毋宁说,从该数值的设定具有技术性、专门性的性质来看,也有可能做这种解释:即便对该数值本身并无认识,只要有对相当于该数值的“含义的认识”即可。与此相反,按照将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理解为客观的处罚条件的观点,甚至对这种“含义的认识”也不需要[24],不仅如此,即便属于医师等专门人员的行为人确信自己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在0. 3毫克以下,仍然可认定存在本罪故意,这种结论是否合适,便值得怀疑。
【注释】
[1]关于客观的处罚条件,包括学说史在内,主要有以下文献:佐伯千仞:“客观的处罚条件”,载佐伯千仞:《刑法中的违法性理论》,1974年版,第149页以下;齐藤诚二:“客观处罚条件之备忘录(一)”,载《成蹊法学》第1号(1969年),第135页以下;堀内捷三:“责任主义与客观的处罚条件”,载《团藤重光博士古稀祝贺论文集·第2卷》,1984年版,第141页以下;曾根威彦:“‘处罚条件’的不法构成机能”,载曾根威彦:《刑事违法论研究》,1998年版,第39页以下;北野通世:“客观的处罚条件论(一)(二)(三)(四)(五)(六)(七·完)”,载《山形大学纪要(社会科学)》,第24卷第1号(1993年)第23页以下、第25卷第1号(1994年)第29页以下、第25卷第2号(1995年)第107页以下、第26卷第1号(1995年)第1页以下、第26卷第2号(1996年)第79页以下、第27卷第1号(1996年)第1页以下、第27卷第2号(1997年)第41页以下;北野通世:“客观的处罚条件”,载西田典之、山口厚、佐伯仁志编:《刑法的争点[第3版]》,2000年版,第32页以下;浅田和茂:“客观的处罚条件”,载西田典之、山口厚、佐伯仁志编:《新·法律学的争点系列刑法的争点》,2007年版,第30页以下;松原芳博:《犯罪概念与可罚性—论客观的处罚条件与一身专属处罚阻却事由》,1997年版,第15页以下;松原芳博:“客观的处罚条件的走向—与盖斯纳的‘客观的处罚条件与责任主义的调和可能性’ 相接—”,载《宫泽浩一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2卷》,2000年版,第99页以下;松原芳博:“破产犯罪的不法构造与成立要件—以实行行为与破产宣告确定之间的‘事实上的牵连关系’为中心”,载《樱井孝一先生古稀祝贺破产法学的轨迹与展望》,2001年版,第483页以下;松原芳博:“构成要件与客观的处罚条件”,载《现代刑事法》第66号(2004年),第46页以下。
[2]日本《刑法》第197条第2款规定了事前受贿罪:“将要成为公务员者,就其将要担任的职务,接受请托,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的,在其就任公务员之时,处5年以下惩役。”—译者注。
[3] 日本《破产法》第265条第1款规定了欺诈破产罪:“不论开始破产程序之前后,出于有害于债权人之目的,实施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的,在针对债务人(针对继承财产的破产,是指继承财产;针对信托财产的破产,是指信托财产。下款同。)的开始破产程序的决定被确定之时,处十年以下惩役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者并科。知情并成为第4项所示行为的相对方的,在开始破产程序的决定被确定之时,处同等刑罚。(一)隐匿或者损坏债务人的财产(针对继承财产的破产,是指属于继承财产的财产;针对信托财产的破产,是指属于信托财产的财产。本条下同。)的行为;(二)伪装债务人的财产的转让或者债务的负担的行为;(三)改变债务人的财产的现状,减损其价格的行为;(四)于债权人不利益地处分债务人的财产,或者债务人负担于债权人不利益的债务的行为。”—译者注。
[4]2004年公布的《新破产法》在其制定之际,究竟是否应该以“决定开始破产程序的确定”作为破产犯罪的处罚要件,曾探讨过这一问题。参见佐伯仁志“破产犯罪”,载《*ト》1273号(2004年),第96页以下。
[5]亲族间盗窃的特例(刑法第244条)等“一身专属性阻却处罚事由”,在与犯罪概念的关系上,存在与客观的处罚条件相同的问题。另外,对“一身专属性阻却处罚事由”,处以“免除刑罚”这一判决形式,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6] 参见佐伯千仞:“客观的处罚条件”,载佐伯千仞:《刑法中的违法性理论》,1974年版,第149页以下;曾根威彦:“‘处罚条件’的不法构成机能”,载曾根威彦:《刑事违法论研究》,1998年版,第48页以下;松原芳博:《犯罪概念与可罚性—论客观的处罚条件与一身专属处罚阻却事由》,1997年版,第225页以下;浅田和茂:“客观的处罚条件”,载西田典之、山口厚、佐伯仁志编:《新·法律学的争点系列刑法的争点》,2007年版,第31页。
[7]参见大判大正6年(1917年)4月19日刑录23辑401页。
[8]Ernst Belig, Die Leher von Verbrechen (1906) , S. 51ff
[9]Ernst Belig, Die Leher von Tatbestand (1930) , S. 1 ff.
[10] 关于这场论争的详细内容,参照松原芳博“犯罪结果与刑法规范”,载《三原宪三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2002年版,第319页以下;曾根威彦“一元的人的不法论及其问题点”,载曾根威彦:《刑事违法论的研究》,1998年版,第3页以下;曾根威彦“二元的人的不法论与犯罪结果”,载曾根威彦:《刑事违法论的研究》,1998年版,第29页以下。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11]参见增田丰:《以规范论再构建责任刑法》,2009年版,第68页以下、第123页以下,等等。
[12]参见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2008年版,第80页以下,等等。
[13]掘内捷三:“责任主义与客观的处罚条件”,载《团藤重光博士古稀祝贺论文集·第2卷》,1984年版,第158页以下。
[14]德国一度认为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是客观的处罚条件,这完全是为了使得认为不需对此存在故意的观点正当化。日本也有观点认为,刑法第108条以及第109条第1项中的“公共危险”是客观的处罚条件,从而试图得出不需要对“公共危险”存在认识这一结论。
[15]参见佐伯千仞:“客观的处罚条件”,载佐伯千仞:《刑法中的违法性理论》,1974年版,第191页。
[16]详见松原芳博:《犯罪概念与可罚性—论客观的处罚条件与一身专属处罚阻却事由》,1997年版,第225页以下。
[17] 除符合客观处罚条件的事实之外,行为状况、身份等情况也是与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具有因果关系的构成要件要素。不同的是,行为状况、身份是行为当时就已经存在的情况,将这种情况定位于构成要件的内部,相对阻力要小,通说也认为这些情况属于构成要件要素。从其实质性根据来看,行为状况与身份可以分为:①法益侵害·危险的基础情况,②对行为人进行责任非难的基础情况,③法益侵害·危险以及对行为人进行责任非难这二者的基础情况。其中,就②③而言,只有存在于行为人的行为当时,才会发挥对行为人的责任奠定基础的作用;而就①而言,可以认为,即便不与行为同时存在,若与行为在时间上、场所上具有一定关系,也能为法益侵害性奠定基础或者提高法益侵害性,作为立法论来说,认为这种情况即便发生在行为之后也可以,做这种立法是有可能的(不过,若与行为之间在时间上、场所上的间隔很大,对针对法益的侵害、危险的贡献度也随之稀薄,因而有必要探讨这种立法形式究竟是否妥当,也要考虑界定处罚范围)。破产犯罪中的“决定开始破产程序的确定”,包括存在于行为当时的情况与发生在行为之后的情况,一起作为针对债权人财产的可罚性程度的危险的基础情况而发挥作用。
[18]行为与客观的处罚条件之间,必须存在“事实上的牵连关系”(针对破产犯罪的最决昭和44年[1969年]10月31日刑集23卷10号1465页、东京地判平成8年[1996年]10月29日判时1597号153页〔参见松原芳博:“欺诈破产罪中不利益处分行为与破产宣告(确定)之间的关系”,载《九州国际大学法学论集》第5卷第1=2号,1999年,第225页〕),这种事实上的牵连关系往往会被理解为是,针对法益的侵害·危险与该事实之间的协同联动。然而,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从该犯罪的违法内容中割离出去,认为它是基于违法外在的政策性考虑的东西,按照这种通说观点无法说明要求存在这种协同联动关系的理由。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19]也有观点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在引以为问题的犯罪的不法内容中,虽不如构成要件要素那样具有基本重要性,但不可否认其属于不法要素”,从而要求对此存在过失(参见林干人:《刑法总论[第2版]》,2008年版,第239页)。然而,该观点在与使用者的关系上,将本年龄规定分类至客观的处罚条件,但这与认为其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观点实质上并无不同。
[20]详见松原芳博:“路上持续停车罪的实行行为、结果以及故意—以最高裁平成15年(2003年)11月21日第二小法庭决定为契机”,载《冈野光雄先生古稀纪念交通刑事法的现代课题》,2007年版,第51页以下。
[21]相反,也有观点将8小时以上的持续停车理解为处罚条件,认为不需要对此存在认识。参见吉田淳一:“路上持续停车违反的故意”,载《警察学论集》第23卷第6号(1970年),第143页。
[22]参见冈野光雄:“醉酒驾驶、携带酒气驾驶的故意”,载冈野光雄:《交通事犯与刑事责任》,2007年版,第40页以下。
[23]参见柏井康夫:“错误”,载《判例夕*》284号(1973年),第99页;堀龙幸男:“道路交通法第119条第1项第7号所规定的携带酒气驾驶罪的故意”,载《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说刑事篇昭和52年度》,1985年版,第287页。
[24]然而,若将“携带酒气”理解为构成要件要素,并要求对此存在认识,与要求对政令所规定的血液中酒精浓度的“含义的认识”相比,在结论上并无多大不同。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内容提要: 日本通说承认客观的处罚条件这一概念,认为其属于无关犯罪成立与否的情况。但是,这切断了犯罪与刑罚要件及其效果之间的联系,有违“犯罪是可罚的行为”这一定义。而且,这种将犯罪从刑罚考量中割离出去的做法,有导致犯罪论的形骸化之虞。事实上,作为发生可罚性程度之危险的介入情况,客观的处罚条件理应还原至作为可罚的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应该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与客观的处罚条件之间的相互联动,由此而导致了法律所应防止的可罚性违法事态的发生。基于这种理解,在行为当时,必须存在将来发生客观的处罚条件的可能性、行为与客观的处罚条件之间的相互联动提高了危险性、对将来发生客观的处罚条件具有预见性。据此,偶然责任得以排除,从而担保了责任主义。
一、问题之所在
日本刑法通说承认,某些情况虽属于实体刑法上的刑罚要件,但并不隶属于“犯罪”概念,并称之为客观的处罚条件[1]。例如,事前受贿罪中的“就任公务员” (刑法第197条第2项[2])、破产诈骗罪中的“开始破产程序的决定的确定”(破产法第265条[3])[4],等等[5]。在通说看来,将要成为公务员的个人只要收受了财物,即成立事前受贿罪,在其正式就任公务员之前,只不过是特别地保留处罚而已。然而,就个人收受财物而言,只要该人尚未正式就任公务员,就不会成为刑罚的处罚对象,即便起诉也是“无罪”,然而,却将此行为评价为“犯罪”,这无疑有违“所谓犯罪,是指能被科处刑罚的行为”这一定义,且切断了犯罪与刑罚要件、效果之间的联系。将要就任公务员的个人收受财物,这一行为究竟是否已具有可罚性程度的违法性,这本身便尚存疑问;若具备了这种违法性,在其就任公务员之前,又为何要保留处罚呢?这一点也不明确。将客观的处罚条件的存在理由满足于单纯的“政策性理由”,不得不说,这无疑是放弃了刑法理论的本来使命。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对此,有观点提出,应将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作为将行为的违法性提高到可罚程度的要素,还原至作为可罚的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6]。但是,此观点就必须回答:与行为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后事实,何以可左右对犯罪行为的违法性评价呢?而且,按照责任主义的要求,应对违法性的基础事实存在故意,然而,认为行为人对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存在故意,这是否合适,也值得探讨。
二、客观的处罚条件与犯罪论
1.犯罪的成立要件与客观的处罚条件
犯罪,是指该当于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说对客观的处罚条件是作消极的定义,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不属于犯罪的成立要件。本节想就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与各个犯罪成立要件之间的关系作些研究,以探讨这些事实是否真的不能属于犯罪成立要件。这同时也意味着,是从反面验证犯罪论体系。
2.构成要件与客观的处罚条件
构成要件首先承担着担保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性机能”,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属于刑罚法规所规定的刑罚要件,理应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对象,这一点应无异议。因而,不待“就任公务员”,便处以事前受贿罪,这不能被允许;由“就任公务员”类推,对担任公共性很高的非公务员职务者也处以事前受贿罪,这就与禁止类推原则相抵触。另外,作为有罪判决理由中必须明示的“应罪事实”(刑事诉讼法第335条),“构成要件”也发挥了刑事诉讼法的机能,事实上,也有判例将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包含在“应罪事实”之内[7]。这样,在具有保障机能与刑事诉讼法机能方面,没有理由将客观的处罚条件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强调构成要件的保障机能的贝林格,尽管在其早期的理论中,将客观的处罚条件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8],但在其晚年的理论中,却认为这些事实属于可将可罚性行为个别化、类型化的,能担保罪刑法定原则的“犯罪类型”要素[9]。
通说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乃至违法有责类型。为此,仅就与违法性的关系而言,构成要件将该罚则所预定的违法事实予以类型化。从这种违法类型化机能来看,构成要件不包括与犯罪的违法性无关的事实。通说将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这一点可能也是其理由之一。对于客观的处罚条件与违法性的关系问题,参见后述。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立足于责任主义,若对该当于构成要件的事实并无认识(或认容),则不能认定具有故意责任。如此,在划定故意的认识对象这一意义上,构成要件具有故意规制机能。但通说认为,不需要对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存在认识(或认容)。也就是,通说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作为不包含在故意的认识对象之内的事实,而将其置于与构成要件要素相对应的位置。然而,为了不以故意为必要,作为便宜之法,而将客观的处罚条件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结论的结论,更让人怀疑这不过是一种伪装,其目的正在于掩盖其本身对责任主义的违反。对于客观的处罚条件与责任的关系问题,参见后述。
3.违法性与客观的处罚条件
通说可能因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是行为之后的外部情况,而将这些事实作为与行为的规范评价无关的情况,从违法性,以至从作为违法性的类型化的构成要件中排除出去。这种理解的背景就在于,针对违法性的实质所采取的规范违反说(行为无价值论)。因为,在规范违反说看来,作为事后的外部情况的客观的处罚条件,与以作用于行为人的意思(意思决定机能)为使命的行为规范毫无关系。围绕“结果”的体系性地位的论争[10]鲜明地反映了规范违反说与客观的处罚条件之间的关系,因而,这里就规范论与结果的体系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做些探讨。
一元的人的不法论通过贯彻规范违反说,将犯罪的“结果”从违法概念中排除出去,使之成为一种客观的处罚条件[11]。一元的人的违法论认为,法规范只有作为命令、禁止作用于人的意思之时,才发挥规制机能,因此,法规范应以反映到行为人主观的现实为前提,不仅无法涉及脱离行为人的手之后的事态即“结果”,让受偶然的情况所左右的“结果”的发生影响到违法,更是有违责任主义。
但是,这种对不法的主观把握以及排除“结果”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夺违法概念的现实性、社会性根基,不得不说,这有违应以社会外界实际发生的事实作为根据的行为主义(Tatprinzip)。而且,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从违法(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中排除出去,也与实定法不相吻合,也就是,实定法中的很多犯罪,是否可罚、可罚程度均取决于结果如何。对此,一元的人的违法论认为,发生的“结果”属于客观的处罚条件,具有证明行为的违法性的机能。但是,行为的违法性才是处罚的根据,若承认这一点,就必须证明行为的违法性已经达到超过合理怀疑的程度,不允许通过“结果”的证明来取而代之。另外,在存在处罚未遂犯规定的犯罪中,原本毋需等到“结果”的发生就能证明行为的违法,并且,由于证明机能本身并不包括决定刑罚轻重的内容,从证明机能也难以说明未遂减轻。如果以可证明未遂情况下的不法程度很低为理由,而减轻其刑,这无非是承认嫌疑刑罚。由此可见,一元的人的不法论并不能说明,刑法为何要规定“结果”的发生。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日本的规范违反说(行为无价值论)的主流立足于二元的人的违法论[12],认为违法评价对象包括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但是,这种观点与作为规范违法说之前提的规范理论却并不协调。规范违反说认为,违法是对具有作用于行为人的意思并控制其行动的机能即行为规范的违反,那么,违法判断就必须是事前判断,不应为行为之后所发生的结果所左右;而且,行为不法以行为规范为内容,结果不法以法益侵害为内容,二者之间并无共通的指导原理,二者在对象、标准、根据等方面均具有不同性质,包含这些不同性质的要素在内的“违法性”概念已扩散到难以对其做出积极性定义。因此,二元的人的不法论也没能在理论上成功地说明“结果”的体系性地位。
为此,要给予形成犯罪的事实性、社会性之根基的“结果”以正当的体系性地位,在违法论上,就不能以作用于行为人意思的命令规范,而只能以否定不恰当事态的评价规范作为其前提,应该采取法益侵害说(结果无价值论),以惹起法益的侵害或危险作为违法性的实质内容。佐伯千仞博士是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还原至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的先驱,正如博士立足于法益侵害说这一点所表明的那样,可以说,这种法益侵害的观点可以提供一种契机,也就是,如同“结果”那样,可以使事前受贿罪中的“担任公务员”等事实与违法产生关联。笔者也是从此方向出发,尝试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还原至违法,这留待后述。
4.责任与客观的处罚条件
通说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本身并非责任要素,这自不待言,就是在不能成为故意的对象这一意义上,也与责任无关。
与通说相反,也有观点主张,应将客观的处罚条件本身作为责任要素还原于犯罪论。该观点从预防目的这一刑事政策的视点重组责任概念,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作为确保刑事政策上的处罚妥当性的事实,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属于纳入了这种刑事政策性考虑的“责任”要素[13]。的确,责任概念与预防目的并不完全对立,也有包含现实的刑事政策性考虑的余地,但是,“责任”概念若包含所有的政策性考虑,就将丧失其内容本身的限定性,也会动摇具有分析性的犯罪论体系。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属于客观的、外部的事态,它所承担的“政策性考虑”未必与行为人的“责任”具有亲和性。
是否需要客观的处罚条件与故意,在与责任主义的关系上成为问题。通过将客观的处罚条件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而认为不需要对此存在认识,这会遭到质疑:是否对责任主义的脱逃与背离呢[14]?对此,通说(处罚限制事由说)作了如下说明: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是对即便没有该事实也具有当罚性的行为予以特别处罚限制的情况,因而,即便没有对该事实的认识(或认容),处罚该行为也并不违反责任主义。也就是说,客观的处罚条件并非是给当罚性奠定基础的要素,而是对已具有当罚性的行为给予要罚性,因而故意不及于此亦可。但是,“限制”处罚与“奠定基础”只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而已,不可能在内容上绝对区分当罚性与要罚性。在这一点上,笔者也抱有怀疑:处罚限制事由说给客观的处罚条件附加故意不及于此这一大前提,这难道不是为了让其结论与责任主义相互调和的“循环论证”而已吗?
另一方面,站在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还原于违法(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的立场,就必须回答:究竟是坚持对客观的处罚条件不需要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将其作为责任主义的例外来说明[15],还是认为至少需要对此存在过失(预见可能性),或者是原则上需要故意(预见)呢?
另外,诸如携带酒气驾驶罪(《道路交通法》第117条之4第2项)那样,可以用具体数值来划定处罚范围的事实,在与是否需要存在认识的关系上,也属于客观的处罚条件,这一点留待后述。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三、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还原至违法(私见[16])
正如前述,法益侵害说认为,以法益侵害或危险为内容的“结果”是违法(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这意味着违法性事后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正如一元的人的不法论所指出的那样,结果发生与否取决于行为后的外部情况。在结果犯中,违法性会事后发生变化,既然对此持肯定态度,那么,对于包含客观的处罚条件的犯罪,也没有理由否定违法性的事后变化。在此观点看来,一般情况下,符合客观的处罚条件的事实,作为将行为所产生的法益的侵害或危险提升到可罚性高度、发生达到法所预定的可罚程度的违法事态即违法结果的中介事实,可将其理解为作为可罚的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将要就任公务员者就将来将要担任的职务收受财物,即便发生了危及公务的公正以及对公务的公正的信赖的危险,但该危险当下仍止于潜在状态,只有当该人实际上就任公务员,从而发生“公务员处于不正当利益的影响之下”这一事态,针对公务的公正及其信赖的危险才会显现出来,才能达到可罚的违法性的程度。“公务员处于不正当利益的影响之下”这一事态并非客体的有形变更,因而在法条的规定形式上,与通常的结果犯有所不同;但它属于以行为为原因之一而产生的与法益相关的事实状态,可认为是(事前)受贿罪中的“结果”。“就任公务员”,这无非是将为发生这种结果而不可或缺的中介事实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予以类型化。
即便是通常的结果犯,利用与行为并无因果关系的外部中介事实而使结果发生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例如,试图杀X,将其绑在铁轨上,X被过往的列车轧死。尽管列车通过这一中介事实是发生死亡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但列车通过这一事实非行为人所能左右,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然而,在将这种预见可能的外部情况作为条件加以利用,而使结果得以发生的场合,只要能认定结果与行为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该结果就归属于行为。不用说,在杀人犯的场合,发生结果并非总需要存在这种中介事实,而且,可以用客体的有形改变来显示结果,因而不能认为这种中介事实属于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与此相反,在事前受贿罪中,一方面,对于发生针对公务员的公正或者对公务员的公正的信赖的达到可罚程度的危险而言,“就任公务员”这一事实就属于不可或缺的事实;另一方面,对这种危险的发生,也难以作确切的描述,因而,通过将“就任公务员”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而描述了可罚的违法事态。至于为何要规定“就任公务员”这一条件,除了是考虑到与这种法益之间的关系之外,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认为“就任公务员”是客观的处罚条件,与违法无关,这种通说观点也未能就作此要求的具体“政策性理由”做出具体说明。若认为在单纯受贿罪(刑法第197条第1项)等犯罪中,“公务员”身份是为法益侵害性奠定基础的构成要件要素,那么,也应认为事前受贿罪中的 “就任公务员”的性质与此并无不同。
笔者的上述观点不时遭到误解,被认为是要求行为者的行为与“就任公务员”等客观的处罚条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而批判笔者的结论并不妥当。但要说明的是,笔者的观点在于:要求行为者的行为与“针对公务的公正或者对公务的公正的信赖的达到可罚程度的危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任公务员”只不过是介入该因果过程的外部条件[17]。
这样,将“就任公务员”作为为了产生针对公务的可罚性危险的事实,而将其还原至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在解释论上就会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行为人收受钱财的时点,必须客观上可以预见到,自己会担任作为请托对象的公务员。按照相当因果关系说,若结果发生所必要的外部客观介入情况属于不能预见,所发生的结果就不能归属于行为。在介入情况属于缺乏客观预见可能性这种程度的异常情况时,就可否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事前受贿罪中的“就任公务员”,其本身尽管与行为并无因果关系,但若在行为的时点,这属于客观预见可能,则收受财物这一行为的作用,与“就任公务员”这一事实的作用相互联动所引起的“针对公务的达到可罚性程度的危险”就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
第二,必须认定存在这样一种关系:收受财物这一行为与“就任公务员”具体协动联动,从而发生了“针对公务的达到可罚性程度的危险”。也就是说,必须存在通过“就任公务员”而使得收受财物这一行为所引发的潜在危险已经显现出来这种关系[18]。为此,作为请托对象的公务与现实担任的公务必须在一般职权的范围内,属于同一公务。而且,在担任公务员的时点,收受财物的效果必须仍在持续。换言之,收受财物之后经过了极长时间、行贿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已经死去、行贿人等相关人员已撤回请托或者已丧失了利害关系之后,再担任公务员的,就不能认定存在因担任公务员而提高了针对公务的危险这一关系,应否定成立事前受贿罪。相反,将“就任公务员”从事前受贿罪的违法内容中割离出去,认为在收受财物的时点已经具备作为该罪的可罚的违法性,按照这种通说的观点,就不可能通过要求该行为与“就任公务员”之间存在协动关系而限定处罚范围。
第三,行为人在收受财物的时点,至少应未必地预见到自己将来会担任作为请托对象的公务员。按照责任主义的要求,要认定行为人具有故意责任,行为人至少必须对该犯罪的违法基础事实存在认识或预见,由于“就任公务员”是成立法所预定的违法事态所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事实,因而,在缺少这种认识或预见时,因对本罪所预定的法益侵害·危险化并不具有认识或预见,就应否定行为人存在故意。就客观的处罚条件而言,要求行为人对此存在认识或预见,这并不现实,前面已探讨了这一前提。但是,就事前受贿罪中的“就任公务员”而言,通常都是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却仍然收受财物,难以想象有对此并无预见者。这是因为,刑法第197条第2项所规定的“将要成为公务员者”,实际上就是指已预见到自己“就任公务员”者,若对“就任公务员”并无预见,也无法理解“将要担任的职务”、“请托”、“贿赂”这些用语的含义。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对破产犯罪中的“开始破产程序的决定的确定”而言—尽管就是否应以此为条件,在立法论上仍有探讨的余地—上述论述也基本适用。
四、以数值划定的要素
从是否故意的对象这一角度,在是否客观的处罚条件这一点上引起争议的,是诸如年龄、浓度、时间、速度等刑罚法规上以数值形式规定的要素。
刑法第176条后段、177条后段规定,对未满13周岁者(不以暴行、胁迫为手段)实施猥亵行为、奸淫行为的,处以强制猥亵罪、强奸罪。这里的问题在于,是否需要认识到对方“未满13周岁”?“未满13周岁”这一事实类型性地描述了该对象没有性的自由决定能力,正是为法益侵害性奠定基础的事实,因而属于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应认为其包含在故意的对象之内。而且,通过外观、口吻、行为方式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判断对方的年龄,因而要求行为人对此存在认识,也并非不现实。
《儿童福利法》将“儿童”定义为“未满18岁周岁者”(第4条),第34条第1项禁止对“儿童”实施法条所规定的特定行为,而且,第34条第1款第4项、第4款之3、第5项禁止对“未满15周岁的儿童”实施法条所规定的特定行为,第60条规定对违反这些禁止规定者科以刑罚。该法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第60条第4款规定,“使用儿童者,不得以不知儿童的年龄为由免除前三条的处罚。但无过失的不在此限”。对此可理解为,承认“未满18周岁”、“未满15周岁”是为行为的违法性奠定基础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使用者”以外的其他人,要求其对此存在认识;对“使用者”科以年龄确认义务,既处罚违反这种确认义务的过失行为,又将该过失的举证责任转嫁至被告人一方。该规定将针对使用者以外的其他人的故意犯与针对使用者的部分过失犯并列在一起,且转换了过失的举证责任,这些是否妥当,尚有探讨的余地,但可以说,该法律是将年龄规定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来对待的[19]。在将“儿童”同样定义为“未满18周岁者”的基础上,处罚那些针对“儿童”实施法条所规定的特定行为(第 4、5、6、7、8条)的《儿童色情法》也规定,“使用儿童者,不得以不知儿童的年龄为由,免除自第5条开始至前条为止所规定的处罚。但无过失的不在此限。”
另外,《有关确保汽车的保管场所等的法律》第11条第2款第2项规定,禁止“汽车在夜间(自日落至日出的时间段)在道路同一场所持续停车8小时以上”,该法第17条第2款第2项规定对违反者科以罚金。最高裁平成15年(2003年)11月21日第2小法庭决定(刑集57卷10号1043页)在认定本罪旨趣在于处罚故意犯的基础上,判定“要成立本罪故意,行为人在停车开始时或者其后,至少必须对超过法定限制时间的持续停车状态存在未必的认识”。由此可以认为,这里的“8小时以上”这一时间要素是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来对待的[20][21]。
《道路交通法》第22条规定,禁止以超过道路标示所指定的最高限速或者政令所规定的最高限速(《道路交通法施行令》第11条规定,汽车在一般道路上的最高时速为60公里)的速度行驶,以该法第118条第 1款第1项(故意犯)与第11条第2款(过失犯)处罚。本罪的故意或过失,只能是就行驶速度这一点而言,从118条分别规定故意犯与过失犯来看,第1款第 1项之罪要求对超过时速60公里存在认识,第2款之罪要求对此存在认识可能性。由此也可理解为,“超过时速60公里”这一要素是构成要件要素而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其次,《道路交通法》第117条之2第1号、第2号规定,就携带酒气驾驶而言,对“含有政令所规定的程度以上的酒精”者予以处罚,《道路交通法施行令》第 44条之3规定其程度为“1毫升血液内含有0.3毫克,或者呼气1升含有0.15毫克”。考虑到会类型性地有碍于安全驾驶,因而规定了该酒精浓度,这应属于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22]。相反,有力观点认为,将该数值包含在故意的对象之内并不合适,应将政令所规定的酒精浓度理解为客观的处罚条件 [23]。但是,将划定行为的可罚的违法性的事实理解为客观的处罚条件,这并不妥当。就行为人的故意而言,对于在驾校接受过培训的驾驶人,理应知道,若饮一定量的酒,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就会超过0.3毫克,要求对此存在未必的故意也并非不现实,毋宁说,从该数值的设定具有技术性、专门性的性质来看,也有可能做这种解释:即便对该数值本身并无认识,只要有对相当于该数值的“含义的认识”即可。与此相反,按照将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理解为客观的处罚条件的观点,甚至对这种“含义的认识”也不需要[24],不仅如此,即便属于医师等专门人员的行为人确信自己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在0. 3毫克以下,仍然可认定存在本罪故意,这种结论是否合适,便值得怀疑。
【注释】
[1]关于客观的处罚条件,包括学说史在内,主要有以下文献:佐伯千仞:“客观的处罚条件”,载佐伯千仞:《刑法中的违法性理论》,1974年版,第149页以下;齐藤诚二:“客观处罚条件之备忘录(一)”,载《成蹊法学》第1号(1969年),第135页以下;堀内捷三:“责任主义与客观的处罚条件”,载《团藤重光博士古稀祝贺论文集·第2卷》,1984年版,第141页以下;曾根威彦:“‘处罚条件’的不法构成机能”,载曾根威彦:《刑事违法论研究》,1998年版,第39页以下;北野通世:“客观的处罚条件论(一)(二)(三)(四)(五)(六)(七·完)”,载《山形大学纪要(社会科学)》,第24卷第1号(1993年)第23页以下、第25卷第1号(1994年)第29页以下、第25卷第2号(1995年)第107页以下、第26卷第1号(1995年)第1页以下、第26卷第2号(1996年)第79页以下、第27卷第1号(1996年)第1页以下、第27卷第2号(1997年)第41页以下;北野通世:“客观的处罚条件”,载西田典之、山口厚、佐伯仁志编:《刑法的争点[第3版]》,2000年版,第32页以下;浅田和茂:“客观的处罚条件”,载西田典之、山口厚、佐伯仁志编:《新·法律学的争点系列刑法的争点》,2007年版,第30页以下;松原芳博:《犯罪概念与可罚性—论客观的处罚条件与一身专属处罚阻却事由》,1997年版,第15页以下;松原芳博:“客观的处罚条件的走向—与盖斯纳的‘客观的处罚条件与责任主义的调和可能性’ 相接—”,载《宫泽浩一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2卷》,2000年版,第99页以下;松原芳博:“破产犯罪的不法构造与成立要件—以实行行为与破产宣告确定之间的‘事实上的牵连关系’为中心”,载《樱井孝一先生古稀祝贺破产法学的轨迹与展望》,2001年版,第483页以下;松原芳博:“构成要件与客观的处罚条件”,载《现代刑事法》第66号(2004年),第46页以下。
[2]日本《刑法》第197条第2款规定了事前受贿罪:“将要成为公务员者,就其将要担任的职务,接受请托,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的,在其就任公务员之时,处5年以下惩役。”—译者注。
[3] 日本《破产法》第265条第1款规定了欺诈破产罪:“不论开始破产程序之前后,出于有害于债权人之目的,实施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的,在针对债务人(针对继承财产的破产,是指继承财产;针对信托财产的破产,是指信托财产。下款同。)的开始破产程序的决定被确定之时,处十年以下惩役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者并科。知情并成为第4项所示行为的相对方的,在开始破产程序的决定被确定之时,处同等刑罚。(一)隐匿或者损坏债务人的财产(针对继承财产的破产,是指属于继承财产的财产;针对信托财产的破产,是指属于信托财产的财产。本条下同。)的行为;(二)伪装债务人的财产的转让或者债务的负担的行为;(三)改变债务人的财产的现状,减损其价格的行为;(四)于债权人不利益地处分债务人的财产,或者债务人负担于债权人不利益的债务的行为。”—译者注。
[4]2004年公布的《新破产法》在其制定之际,究竟是否应该以“决定开始破产程序的确定”作为破产犯罪的处罚要件,曾探讨过这一问题。参见佐伯仁志“破产犯罪”,载《*ト》1273号(2004年),第96页以下。
[5]亲族间盗窃的特例(刑法第244条)等“一身专属性阻却处罚事由”,在与犯罪概念的关系上,存在与客观的处罚条件相同的问题。另外,对“一身专属性阻却处罚事由”,处以“免除刑罚”这一判决形式,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6] 参见佐伯千仞:“客观的处罚条件”,载佐伯千仞:《刑法中的违法性理论》,1974年版,第149页以下;曾根威彦:“‘处罚条件’的不法构成机能”,载曾根威彦:《刑事违法论研究》,1998年版,第48页以下;松原芳博:《犯罪概念与可罚性—论客观的处罚条件与一身专属处罚阻却事由》,1997年版,第225页以下;浅田和茂:“客观的处罚条件”,载西田典之、山口厚、佐伯仁志编:《新·法律学的争点系列刑法的争点》,2007年版,第31页。
[7]参见大判大正6年(1917年)4月19日刑录23辑401页。
[8]Ernst Belig, Die Leher von Verbrechen (1906) , S. 51ff
[9]Ernst Belig, Die Leher von Tatbestand (1930) , S. 1 ff.
[10] 关于这场论争的详细内容,参照松原芳博“犯罪结果与刑法规范”,载《三原宪三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2002年版,第319页以下;曾根威彦“一元的人的不法论及其问题点”,载曾根威彦:《刑事违法论的研究》,1998年版,第3页以下;曾根威彦“二元的人的不法论与犯罪结果”,载曾根威彦:《刑事违法论的研究》,1998年版,第29页以下。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11]参见增田丰:《以规范论再构建责任刑法》,2009年版,第68页以下、第123页以下,等等。
[12]参见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2008年版,第80页以下,等等。
[13]掘内捷三:“责任主义与客观的处罚条件”,载《团藤重光博士古稀祝贺论文集·第2卷》,1984年版,第158页以下。
[14]德国一度认为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是客观的处罚条件,这完全是为了使得认为不需对此存在故意的观点正当化。日本也有观点认为,刑法第108条以及第109条第1项中的“公共危险”是客观的处罚条件,从而试图得出不需要对“公共危险”存在认识这一结论。
[15]参见佐伯千仞:“客观的处罚条件”,载佐伯千仞:《刑法中的违法性理论》,1974年版,第191页。
[16]详见松原芳博:《犯罪概念与可罚性—论客观的处罚条件与一身专属处罚阻却事由》,1997年版,第225页以下。
[17] 除符合客观处罚条件的事实之外,行为状况、身份等情况也是与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具有因果关系的构成要件要素。不同的是,行为状况、身份是行为当时就已经存在的情况,将这种情况定位于构成要件的内部,相对阻力要小,通说也认为这些情况属于构成要件要素。从其实质性根据来看,行为状况与身份可以分为:①法益侵害·危险的基础情况,②对行为人进行责任非难的基础情况,③法益侵害·危险以及对行为人进行责任非难这二者的基础情况。其中,就②③而言,只有存在于行为人的行为当时,才会发挥对行为人的责任奠定基础的作用;而就①而言,可以认为,即便不与行为同时存在,若与行为在时间上、场所上具有一定关系,也能为法益侵害性奠定基础或者提高法益侵害性,作为立法论来说,认为这种情况即便发生在行为之后也可以,做这种立法是有可能的(不过,若与行为之间在时间上、场所上的间隔很大,对针对法益的侵害、危险的贡献度也随之稀薄,因而有必要探讨这种立法形式究竟是否妥当,也要考虑界定处罚范围)。破产犯罪中的“决定开始破产程序的确定”,包括存在于行为当时的情况与发生在行为之后的情况,一起作为针对债权人财产的可罚性程度的危险的基础情况而发挥作用。
[18]行为与客观的处罚条件之间,必须存在“事实上的牵连关系”(针对破产犯罪的最决昭和44年[1969年]10月31日刑集23卷10号1465页、东京地判平成8年[1996年]10月29日判时1597号153页〔参见松原芳博:“欺诈破产罪中不利益处分行为与破产宣告(确定)之间的关系”,载《九州国际大学法学论集》第5卷第1=2号,1999年,第225页〕),这种事实上的牵连关系往往会被理解为是,针对法益的侵害·危险与该事实之间的协同联动。然而,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从该犯罪的违法内容中割离出去,认为它是基于违法外在的政策性考虑的东西,按照这种通说观点无法说明要求存在这种协同联动关系的理由。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19]也有观点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在引以为问题的犯罪的不法内容中,虽不如构成要件要素那样具有基本重要性,但不可否认其属于不法要素”,从而要求对此存在过失(参见林干人:《刑法总论[第2版]》,2008年版,第239页)。然而,该观点在与使用者的关系上,将本年龄规定分类至客观的处罚条件,但这与认为其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观点实质上并无不同。
[20]详见松原芳博:“路上持续停车罪的实行行为、结果以及故意—以最高裁平成15年(2003年)11月21日第二小法庭决定为契机”,载《冈野光雄先生古稀纪念交通刑事法的现代课题》,2007年版,第51页以下。
[21]相反,也有观点将8小时以上的持续停车理解为处罚条件,认为不需要对此存在认识。参见吉田淳一:“路上持续停车违反的故意”,载《警察学论集》第23卷第6号(1970年),第143页。
[22]参见冈野光雄:“醉酒驾驶、携带酒气驾驶的故意”,载冈野光雄:《交通事犯与刑事责任》,2007年版,第40页以下。
[23]参见柏井康夫:“错误”,载《判例夕*》284号(1973年),第99页;堀龙幸男:“道路交通法第119条第1项第7号所规定的携带酒气驾驶罪的故意”,载《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说刑事篇昭和52年度》,1985年版,第287页。
[24]然而,若将“携带酒气”理解为构成要件要素,并要求对此存在认识,与要求对政令所规定的血液中酒精浓度的“含义的认识”相比,在结论上并无多大不同。 教师职称论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