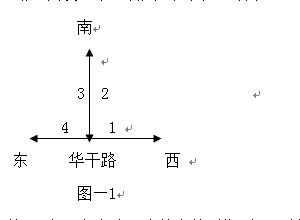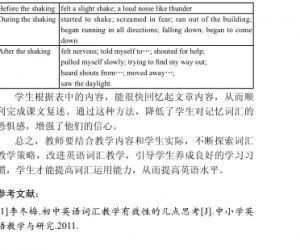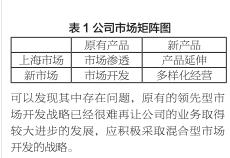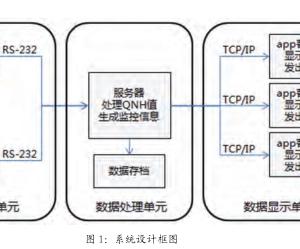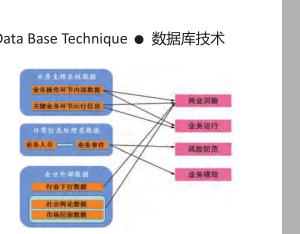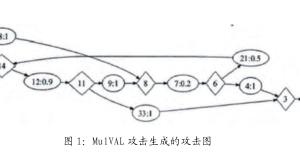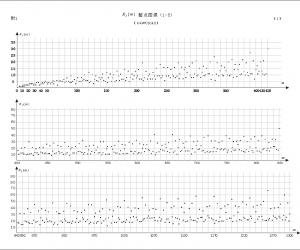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
【摘要】: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史学实践中,有着重要影响。作者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一书中,自如运笔,简明扼要地将年鉴派的一轮花甲历程,分析的丝丝入扣。此书优长,在乎言简意赅,然限于篇幅,于学派所当论者,亦多缺遗。故是书所无者,如学术政治、兴起背景、可能之写作手法等,皆应为读者知。
【关键词】:年鉴派 《法国史学革命》 内在理路 学术政治
一、“入局”与“旁观”,作者的冷静叙述。
记得刘少奇有句论“批评”的名言—优点讲够,缺点讲透。所论确当,不过,若不能“深味”批评对象,恐怕难以做到“讲够”、“讲透”。作者彼得·伯克自言“我有时将自己说成年鉴派的‘同路人’,也就是说,一个(像许多其他外国历史学家一样)受这一运动启发的局外人。近三十年来,我相当紧密地追随着它的命运。”[①](文内若无特殊说明,所引内容皆出自《法国史学革命》)彼得·伯克虽将其界定为“局外人”,但又说“我相当紧密地追随着它的命运”。而且作者亦曾访问年鉴学派的重要人物,并与之保持联系。所以称其为“入局”,亦未尝不可。彼得·伯克接着说:“尽管如此,剑桥与巴黎之间的距离,还是远到了足以(由我来)撰写一本评价年鉴派成就的史书。”此外,在本书“鸣谢”部分,他还写道:“跟我一样,他们力求在与年鉴派打交道的同时,与它保持一定距离。”所以由此看,作者写此书,也可称之为“旁观”。因恐著史为现实裹胁,且“尘埃落定”,历史方可“水落石出”。故向有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说法。不过,因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所以比之后辈,历史的亲历者,往往更易对往昔之其人、其事,抱有“了解之同情”,这也是“入局”撰史的优长。凭藉“入局”,作者自如运笔,简明扼要地将年鉴派的一轮花甲历程,分析的丝丝入扣。复因“旁观”,作者亦能保持客观,正如书中所说“人们可以说,布洛赫对英国史的兴趣及其对克制性陈述的酷爱,让他多少被视为荣誉英国人。”作者在书中总是小心翼翼地抛出某个前提,以使其叙述免于偏执与武断。如作者用一句“尽管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两人都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但是接下来的部分基本上不会谈到运动的这一侧面—比方说,索邦与高等研究院之间的竞争,或是为控制职位和课程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便巧妙地限定了写作内容。考虑到另一本由弗朗索瓦·多斯撰写的研究年鉴派的重要作品--《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②]中对学术政治的大量描写。我们似可认为彼得·伯克的“这一巧妙限定”甚至影响了全书风格—显然这比多斯的作品要多些“书卷气”。“旁观”的彼得·伯克,在文中,特别是在第五章“全球视野下的年鉴派”中,亦道出了学派的不足与局限。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反映法国特性的不足与局限,也是全球视野下,学派“独特价值”之所在。毕竟年鉴派以法语思考、用法语写作,它应对的是法国历史文化。是故,它的课题、方法与史观,皆是对法国性的史学展现。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植根于法国命运的年鉴派,其优劣是非,皆需以法国实际为第一标准。年鉴派的胜利,正在于它切合了法国的历史逻辑,它不必也不能去顺应其它国家的历史逻辑。作为承受方,我们应以“接受启发”而非“照抄照搬”的态度,去观察年鉴派的海外影响。所以年鉴派首先是“法国史学革命”,这场运动实质上是在法国情境、逻辑下,对法国旧史学的反动,运动的一切皆规定于法国性。
在所有介绍年鉴学派的著作中,《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恐怕是最精炼的一本。作者说:“本书的目的是描述、分析和评价年鉴派的成就。”还说:“本书只能勉强算是思想史研究。它并不奢望成为研究年鉴运动的权威的学术论著,我希望21世纪会有人来做这份工作。”显然,身为“新文化史”的旗手,彼得·伯克在此无意自谦,只是作为其非代表作,作者确也不愿穷竭心血。不过,诚如冯友兰所言,“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③]所以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史学界介绍、评价年鉴派学术成就的最佳入门书。”
二、过分的“内在理路”依赖,使全书缺乏时代与社会感
全书虽以短精致胜,但有限的篇幅,也制约了内容的扩展。客观地说,在作者英式克制叙述中,年鉴派的不少内容只好无奈缺席。加之,作者欲主以叙事,故于概括着墨无几,且不喜分析,言及学派起承转合处,一味从“学术”里寻,给人就事论事之感,殊不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通篇读来,只见一“脱离”社会与时代的年鉴派。论起写作思路,本书倒极合余英时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说。余英时认为思想史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我们可从思想自身的变迁中寻出其前后阶段演化的内在线索。[④]这多少使人想起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内外因原理。不过,余英时自言“内在理路”“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⑤]。但他也补充道:“我在本书中虽然采取了‘内在理路’的观点,但是我并未将它与‘外缘影响’对立起来。”“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缘解释,而且也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⑥]据此看,学术创新不必意味着对旧有认识和范式的全盘否定,事实上,就创新与“旧有”的关系,创新可分为积极的创新、消极的创新两类,应鼓励积极的创新,即那些融通“旧有”而非建立在“传统的废墟”之上的创新。有理由相信,彼得·伯克有能力将本书内容组织的更为丰富。不过,因篇幅所限和其它一些未言明的所在,作者拒绝了这一可能的诱惑。作者将其首章题为“历史编撰学旧体制及其批评者”,正体现了本书写作的“内在理路”取向。不错,索邦旧史学的“束缚”和社会科学提供的路径,确实构成了年鉴运动兴起的学术要因。不过,从“长镜头”和“大景深”的角度看,本书确实忽略了分析年鉴派与时代和社会大势间的关系。
一战摧毁了近代以来西方人乐观的进步主义观念和对人类理性及光辉人性的坚信,使欧洲人产生了幻灭感。于是,历史学家们开始注意研究战争根源,并逐步将关注范围扩大至政府政策或外交协商过程之外的各种力量。如此,史学的研究范围在一战后逐步开始扩大。接着,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给整个西方社会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恐慌和怀疑心理。这进一步推动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们去反思旧有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这时,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学科细化、专业化、制度化后,开始重新出现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意识。时人声称“经济历史,我们时代的统一的人文科学,产生于1929年和1930年初,即世界范围痛苦的危机之中。”[⑦]
应该来讲,这些社会与思潮的变迁,作为所谓的“外缘因素”,都刺激着史学家对史学传统、研究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而且也推动了年鉴派所借重的各类社会科学的发展。但在书中,这些联系都被省略了,作者笔下是一“年鉴派之年鉴派”,而非“历史、法国之年鉴派”,这不能不说是一遗憾。
三、拒绝民族志诱惑,即是忽略学术政治?
如前记,作者在文中早早声明,“我也多少带着遗憾,抵制了撰写布勒瓦·拉斯派尔街54号居民—他们的祖先、联姻、派别、庇护与被庇护的网络、生活方式、心态等等—的民族志研究的诱惑。”不错,民族志的诱惑被摈斥了,不过,我有时想,作者既能“入局”,若节制地增加些传记色彩,并对年鉴派集体心态进行适可而止的探讨,或许更为有趣。谨慎的心态史研究和有分寸的传记描写,实际上可解构任何被神化的存在。或年鉴派果真可当得起一句“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论着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但历史是由人创造和书写的,史学史也是作为人的史学家的学术实践。所以,深入史学家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将其学术活动还原为其现实生活和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这时,我们发现,由时空距离造成的形象放大,将不复存在。所以心态研究、传记写作,在一定情况下,应当“祛魅”。以年鉴派为例,在其“一整个书架的出色著作”背后,是学术政治的大行其道。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年鉴派史家绝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们关切政治,以权力为其研究开路。作者尽管预先声明,本书不关心学术政治。但彼得·伯克还是用“费弗尔控制权力”、“布罗代尔控制权力”两个短条目,对其学术政治做了简要交代。作为关心年鉴派的读者,我们有必要知道的更多。在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中。我们可发现以年鉴派为例的“学术生产”。年鉴派重视夺取出版、传媒阵地,并以此作为学术打压和扩张的得力手段。“年鉴学派的成员夺取了传媒社会的所有关键岗位。……大多数出版社负责历史丛书的都是年鉴学派的人。他们身居要职,大权在握:哪些著作能够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宫,全由他们定夺。享有霸权地位的年鉴学派还控制着新闻机构,并用其宣传自己的出版物,从而保证其影响和争取更多公众。从研究实验室到发行渠道,法国的史学生产几乎都被年鉴学派所垄断。”此外,年鉴派也深谙交结权贵之道。权力只向找准位置的人开放,幸运的是,年鉴派有自知之明,它选择了知识。“历史和权力向来密切相关。20世纪的权力与以往有所不同,年鉴学派的力量在于成功地依附于这些新型权力。而权力则利用历史学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历史学家将某种意义赋予政权,并成为其合法性的担保人。”事实上,后期的《年鉴》杂志与银行家、金融家、资产阶级政客和技术官僚们的关系日渐密切,而这些人正是政府倚重的力量。我们还应知道的是,社会科学不仅通过向年鉴派提供理论,也以提出挑战的方式,推动着其发展。实际上,年鉴派的某些观点是为论战而提出的,如布罗代尔为对抗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