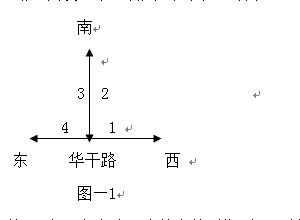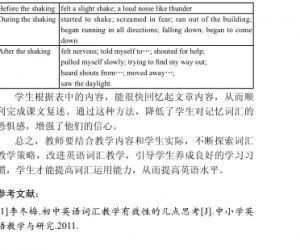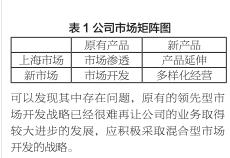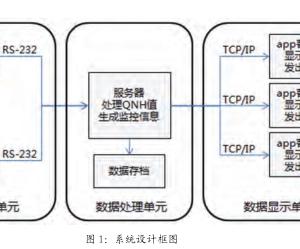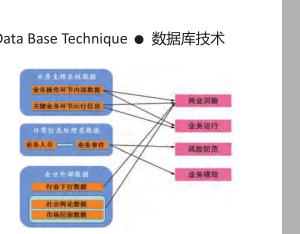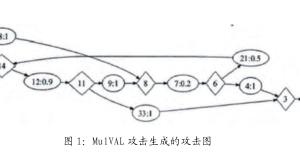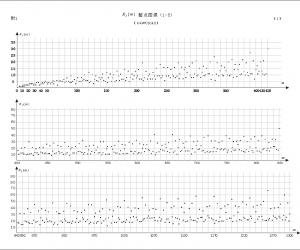试析网络空间跨文化传播中“交流的无奈” —读彼得斯《交流的无奈》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网络传播 文化认同 文化冲突 交流困境
论文摘要:跨文化网络传播是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生存境遇,对人的文化生存带来诸多影响。在这些文化影响中,文化认同危机的加剧、文化冲突的易发性等问题构成了网络空间跨文化“交流的无奈”。这种交流困境的存在可以从全球化的文化影响以及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加以解释。摆脱这种交流的困境,跨文化网络传播也需走向伦理结构。发表论文网
如今,没有谁会否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地域性界限不断地被打破以及跨国、跨地区之间各种往来的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彼此之间“相遇”和“交流”的渴望也日益迫切。这正如上世纪末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彼得斯 (John Durham Peters)在佼流的无勘一书中预言的“‘交流’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越是看不见的东西,渴望便越是迫切”。如何发表论文
1990年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又为跨文化传播构筑起全新的场域—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加速流动,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信息接触量与日俱增,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景观经由网络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焦点,世界在人们面前加速呈现。在网络中,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个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整合于一个平台,网络建构了一个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空间,提高了人类跨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交锋、碰撞日益加深。网络似乎“从技术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文化间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信息的流动达到一个新阶段,但它同时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难度。彼得斯早就对所谓 “技术说”的乐观主义倾向提出过批判,“今天有关交流的紧迫问题一—时空的远望(如因特网)、经验和身份的复制(如虚拟现实)—在过去的年代,就曾以类似的方式探索过了”,在他看来,这种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交流难度的增加并非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对原本就存在的障碍的“扩大”,或者是使某种希望在最基本意义上的再次“落空”。
于是,不得不怀疑人们对跨文化网络传播所做的浪漫期盼只是一种新技术到来时常患的“欣快症”。互联网技术虽然进一步强化了詹姆斯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中央转换器”的作用,在接触层面上增加了文化间的交往机会和频率,或重或轻地在“唯我论”所宣扬的那堵无法逾越的“心灵之墙”上凿穿了几个小孔,但这种交往方式的改变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基本困境。网络绝非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可以将隔阂一捅就破的“传心术”,在本原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法直达心底或真正分享内心经验;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仍被重重迷雾所围绕,无法绕开“交流”所固有的“宏大而哀婉”的属性。
一、数字化文化冲突如期上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融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几乎没有一种本土文化能够固守自己的边界而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间的吸引渗透促使每一种文化做出一定的调适甚至转型,当某种文化打上了异质文化的标记时,文化融合便发生了。在自主选择和均衡传播下发生的文化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自然的过程,它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就这一层面而言,网络空间整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形态,技术的融合的确增加了文化融合的机会。
然而,文化融合必定要经历各种文化缓冲体的抵御,特别是处于文化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情感定式、思维方式等,这些往往难以穿破。“网络交往中虚拟身份依然可以演绎出多重交流情境,但现实文化身份还是起到统摄的作用,越是深人的交往,越是能接近面具背后的真实脸孔”。彼得斯曾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交流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于人自身,人们真正担心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或文化的降格,……,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速之客。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原本就存在着许多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无奈”,上述基于不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差异正是彼得斯所言“内心深处不速之客”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构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
在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的相互吸引渗透并未轻易逾越文化深层的基础结构。网际交往虽然以在线身份来进行,但虚拟文化身份背后的真实文化身份却起到制约与统摄的作用。近年来,以黑客攻击、网络抵制为代表的跨国网络传播事件凸显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植根于现实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化差异并未因数字代码的兼容性而被抹平”。因此,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交往并没有真正打破现实的藩篱,文化深层结构的排他哇导致跨文化冲突难以避免,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换了种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现。
二、文化认同难逃“离散化”梦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认同是另一个核心问题。“文化认同是指文化身份的确认过程,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个体进行文化定位、避免文化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对处于跨文化传播情境中的人来说,文化认同可以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应该说,依靠文化接近性形成的在线聚集是跨文化网络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处于跨文化情境中的人可以通过在线社区来与原有文化保持不断的联结,从而在新的旅居者文化身份和既有的文化身份之间建立一定的平衡。
然而,彼得斯指出,“大众传媒的常规观念捕捉到的,仅仅是巨型信息系统中异化的潜在趋势,而不是人际魅力的多重技巧”,这段话的背景虽然是针对20世纪50 年代造就的“大众传播”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相比所存有的缺陷,却也应验了当今网络空间跨文化传播的尴尬—尽管就技术而言,网络提供了一种高效便捷的文化调适方式,但这毕竟是一种虚拟的联结,“传媒和信息交流网在提供文化交流的非地域性的同时让我们轻信一种近邻性,而这种近邻性则是一种假象、一个陷阱。
文化认同的危机不仅从未在跨文化网络传播中消失,而且伴随着现实社会深度文化依存的打破,在网络空间中反而不断加剧。在网上,人们通过建立各种虚拟社区发展出一些新型的文化交往方式,这些虚拟社群逐渐替代传统的社交场合成为最新的亚文化培育场所,并且不断地向现实空间延伸其利益诉求。在网际交往中,身体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在交往结构中的位置,主体的构型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信息方式把主体重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非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地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在网络中,构建和发展新型的文化身份变得十分容易,文化认同走向多重化和离散化,有学者指出,“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的流动加速变得十分普遍,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型的、拼接型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
三、网络传播:反思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面视镜
跨文化网络传播可以将现实交往关系延伸到网络空间,以产生跨时空的高效迅捷模式。网际交往不仅是对现实交往的延伸,还是一种“数字化”的创造,它可以生产出具有网络文化特征的虚拟交往方式。于是,跨文化传播的所有关切问题都集聚在网络空间,演绎出跨文化网络传播的复杂格局。
由此,我们需要拨开迷雾见本质—跨文化网络传播的核心是技术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解除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是达至跨文化传播目标的前提,然而传播技术改变的只是文化的表现形态,处于文化深层的心理结构作为历史的建构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网络空间并不能造成现实文化基础架构的崩塌和重组。跨文化网络传播延续了“交流的无奈”,这并不是技术导致的结果,而有其文化的根源。无怪乎彼得斯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有当代人才会在“交流”问题上有如此的焦虑,他们彼此虽近在咫尺,却又相距万里!”
然而,交流的失败并非必然导致悲观的结论,彼得斯在书中再三重申,“交流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孤魂野鬼,渴望搜寻灵魂伴侣的孤魂野鬼;而是意味着我们有新的办法彼此联系,共同开辟新的天地” “‘交流’的尝试即使终归徒劳也不值得扼腕叹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交流的失败带来的是对人类本质问题的思考,是寻求新认识,并以此来看待和化解交流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的可能性”。
网络没有为跨文化传播开拓乐观主义的前景,但却成为了反思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面视镜。彼得斯在对传播思想史进行梳理时指出,交流转向的基本路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对方为中心;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他人、影响他人,而是认识他人的特性;不是固守自身思想的传递,而是选择一种能让对方理解的说话方式。这一点对于跨文化传播的伦理建构而言可谓振聋发馈 “一个体现为伦理合法性的跨文化传播,应强调每一个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谋求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之间建立某种具有主体间性的相互关系;应强调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或许,“如果我们能多一些‘手拉手’,少一些‘心连心’,不因无法连心而拒绝拉手,更不是为了连心而使劲拉手”,我们的交流会更顺利、更轻松而且更充满乐趣。
论文摘要:跨文化网络传播是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生存境遇,对人的文化生存带来诸多影响。在这些文化影响中,文化认同危机的加剧、文化冲突的易发性等问题构成了网络空间跨文化“交流的无奈”。这种交流困境的存在可以从全球化的文化影响以及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加以解释。摆脱这种交流的困境,跨文化网络传播也需走向伦理结构。发表论文网
如今,没有谁会否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地域性界限不断地被打破以及跨国、跨地区之间各种往来的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彼此之间“相遇”和“交流”的渴望也日益迫切。这正如上世纪末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彼得斯 (John Durham Peters)在佼流的无勘一书中预言的“‘交流’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越是看不见的东西,渴望便越是迫切”。如何发表论文
1990年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又为跨文化传播构筑起全新的场域—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加速流动,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信息接触量与日俱增,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景观经由网络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焦点,世界在人们面前加速呈现。在网络中,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个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整合于一个平台,网络建构了一个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空间,提高了人类跨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交锋、碰撞日益加深。网络似乎“从技术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文化间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信息的流动达到一个新阶段,但它同时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难度。彼得斯早就对所谓 “技术说”的乐观主义倾向提出过批判,“今天有关交流的紧迫问题一—时空的远望(如因特网)、经验和身份的复制(如虚拟现实)—在过去的年代,就曾以类似的方式探索过了”,在他看来,这种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交流难度的增加并非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对原本就存在的障碍的“扩大”,或者是使某种希望在最基本意义上的再次“落空”。
于是,不得不怀疑人们对跨文化网络传播所做的浪漫期盼只是一种新技术到来时常患的“欣快症”。互联网技术虽然进一步强化了詹姆斯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中央转换器”的作用,在接触层面上增加了文化间的交往机会和频率,或重或轻地在“唯我论”所宣扬的那堵无法逾越的“心灵之墙”上凿穿了几个小孔,但这种交往方式的改变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基本困境。网络绝非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可以将隔阂一捅就破的“传心术”,在本原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法直达心底或真正分享内心经验;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仍被重重迷雾所围绕,无法绕开“交流”所固有的“宏大而哀婉”的属性。
一、数字化文化冲突如期上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融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几乎没有一种本土文化能够固守自己的边界而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间的吸引渗透促使每一种文化做出一定的调适甚至转型,当某种文化打上了异质文化的标记时,文化融合便发生了。在自主选择和均衡传播下发生的文化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自然的过程,它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就这一层面而言,网络空间整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形态,技术的融合的确增加了文化融合的机会。
然而,文化融合必定要经历各种文化缓冲体的抵御,特别是处于文化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情感定式、思维方式等,这些往往难以穿破。“网络交往中虚拟身份依然可以演绎出多重交流情境,但现实文化身份还是起到统摄的作用,越是深人的交往,越是能接近面具背后的真实脸孔”。彼得斯曾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交流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于人自身,人们真正担心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或文化的降格,……,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速之客。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原本就存在着许多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无奈”,上述基于不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差异正是彼得斯所言“内心深处不速之客”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构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
在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的相互吸引渗透并未轻易逾越文化深层的基础结构。网际交往虽然以在线身份来进行,但虚拟文化身份背后的真实文化身份却起到制约与统摄的作用。近年来,以黑客攻击、网络抵制为代表的跨国网络传播事件凸显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植根于现实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化差异并未因数字代码的兼容性而被抹平”。因此,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交往并没有真正打破现实的藩篱,文化深层结构的排他哇导致跨文化冲突难以避免,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换了种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现。
二、文化认同难逃“离散化”梦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认同是另一个核心问题。“文化认同是指文化身份的确认过程,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个体进行文化定位、避免文化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对处于跨文化传播情境中的人来说,文化认同可以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应该说,依靠文化接近性形成的在线聚集是跨文化网络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处于跨文化情境中的人可以通过在线社区来与原有文化保持不断的联结,从而在新的旅居者文化身份和既有的文化身份之间建立一定的平衡。
然而,彼得斯指出,“大众传媒的常规观念捕捉到的,仅仅是巨型信息系统中异化的潜在趋势,而不是人际魅力的多重技巧”,这段话的背景虽然是针对20世纪50 年代造就的“大众传播”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相比所存有的缺陷,却也应验了当今网络空间跨文化传播的尴尬—尽管就技术而言,网络提供了一种高效便捷的文化调适方式,但这毕竟是一种虚拟的联结,“传媒和信息交流网在提供文化交流的非地域性的同时让我们轻信一种近邻性,而这种近邻性则是一种假象、一个陷阱。
文化认同的危机不仅从未在跨文化网络传播中消失,而且伴随着现实社会深度文化依存的打破,在网络空间中反而不断加剧。在网上,人们通过建立各种虚拟社区发展出一些新型的文化交往方式,这些虚拟社群逐渐替代传统的社交场合成为最新的亚文化培育场所,并且不断地向现实空间延伸其利益诉求。在网际交往中,身体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在交往结构中的位置,主体的构型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信息方式把主体重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非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地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在网络中,构建和发展新型的文化身份变得十分容易,文化认同走向多重化和离散化,有学者指出,“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的流动加速变得十分普遍,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型的、拼接型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
三、网络传播:反思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面视镜
跨文化网络传播可以将现实交往关系延伸到网络空间,以产生跨时空的高效迅捷模式。网际交往不仅是对现实交往的延伸,还是一种“数字化”的创造,它可以生产出具有网络文化特征的虚拟交往方式。于是,跨文化传播的所有关切问题都集聚在网络空间,演绎出跨文化网络传播的复杂格局。
由此,我们需要拨开迷雾见本质—跨文化网络传播的核心是技术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解除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是达至跨文化传播目标的前提,然而传播技术改变的只是文化的表现形态,处于文化深层的心理结构作为历史的建构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网络空间并不能造成现实文化基础架构的崩塌和重组。跨文化网络传播延续了“交流的无奈”,这并不是技术导致的结果,而有其文化的根源。无怪乎彼得斯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有当代人才会在“交流”问题上有如此的焦虑,他们彼此虽近在咫尺,却又相距万里!”
然而,交流的失败并非必然导致悲观的结论,彼得斯在书中再三重申,“交流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孤魂野鬼,渴望搜寻灵魂伴侣的孤魂野鬼;而是意味着我们有新的办法彼此联系,共同开辟新的天地” “‘交流’的尝试即使终归徒劳也不值得扼腕叹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交流的失败带来的是对人类本质问题的思考,是寻求新认识,并以此来看待和化解交流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的可能性”。
网络没有为跨文化传播开拓乐观主义的前景,但却成为了反思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面视镜。彼得斯在对传播思想史进行梳理时指出,交流转向的基本路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对方为中心;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他人、影响他人,而是认识他人的特性;不是固守自身思想的传递,而是选择一种能让对方理解的说话方式。这一点对于跨文化传播的伦理建构而言可谓振聋发馈 “一个体现为伦理合法性的跨文化传播,应强调每一个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谋求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之间建立某种具有主体间性的相互关系;应强调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或许,“如果我们能多一些‘手拉手’,少一些‘心连心’,不因无法连心而拒绝拉手,更不是为了连心而使劲拉手”,我们的交流会更顺利、更轻松而且更充满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