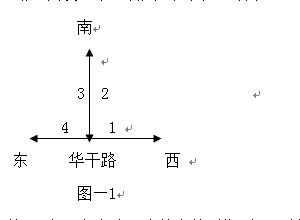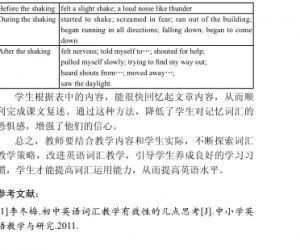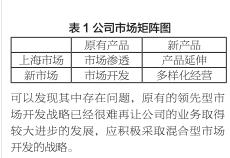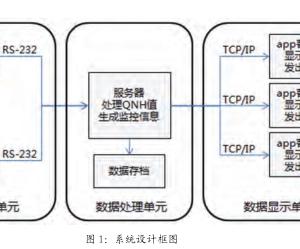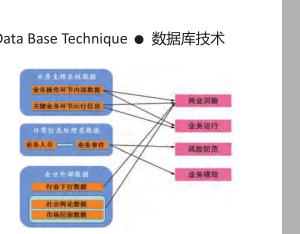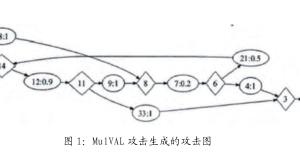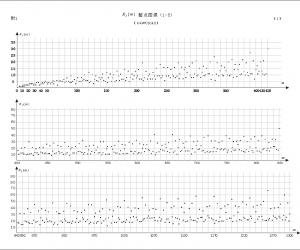万国公法引入与明治初年的日朝关系
万国公法引入与明治初年的日朝关系
邹皓丹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100871)
摘要:明治初年,万国公法成为明治政府外交上的指导思想,以万国公法为原则,日朝关系经历了从传统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的转变。其中,宫本小一的《朝鲜论》批驳了政府旧有的外交观念,要求重新在国际法秩序的基础上认识日朝关系,奠定了日本吞并朝鲜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万国公法,日朝关系,宫本小一,《朝鲜论》
一、万国公法下的条约体制
1853年美舰叩关,《日美亲善条约》签订,日本被迫卷入以条约体制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中,“夷狄禽兽之异人,携文明利器胁迫开港,言必称国际法。”[1]幕府开国,外交成为事关独立大业的核心问题。鉴于此,“万国公法(国际法)思想成为开国论的指导原理,……也成为当局必须研究的功课。”[2]事实上,它也是日本“最初移入的欧美法制思想。”[3]
明治维新之初,百废待举,面临对内建立中央集权、振兴经济、文明开化,对外修正不平等条约、获得国家完全独立的双重改革任务。新政府不但接受了万国公法,并且将其作为外交行为的准则。这就赋予了《万国公法》于知识以外的政治含义。“西洋的公法在当时恰恰犹如宗教的经典,以权威的身份获得广泛阅读。”[4] 因此明治元年正月,天皇以敕令的名义通知各国公使“外国交际之仪,以宇内之公法处理,”同年二月示谕“斟酌采用皇国固有之国体与万国公法”接待外国公使来朝。[5]
特别是1865年东京开成翻译所翻刻了中文版《万国公法》,“日译本、训读本、训点本、注释本也相继出版,”[6]它对于日本政界、学界了解万国公法具有重大意义,“自此我锁国独栖之公民开始了解与各国交流之条规,有识之士争相阅读。”[7]分释义明源、论诸国自然之权、论平时往来、论交战等四卷,以东方人的思维诠释了西方的条约体制,得到广泛传播。
江户幕府时代,日本闭关锁国,其国际交往仅限于两个通商国(中国、荷兰)和两个通信国(琉球、朝鲜)之间,其交际方式亦沿用了以中国为天朝上国的朝贡体制模式。万国公法为载体的西方条约体制于幕末传入日本,它与幕府传统的国际交往方式完全不同,前者体现了法秩序为核心的近代国际观,而后者则是发源于中国封建秩序下的礼仪制度。
首先,《万国公法》中强调国家为单位行使主权。何谓主权?“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此上权或行于内、或行于外。行于内,则依各国之法度,或寓于民,或归于君。……主权行于外者,即本国自主而不听命于他国也,各国平战、交际皆凭此权。”[8]由此可见,主权的意义,在于对内的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的独立外交权,它是万国公法的最基本旨归。
其次,根据惠顿的《万国公法》,以主权的完整程度而言,国家分为自主之国与半自主之国。自主之国,即“无论何等国法,若能自治其事儿不听命于他国,则可谓自主矣。……就公法而论,自主之国,无论其国势大小,皆平行也。一国遇事,若偶然听命于他国,或常请议于他国,均与主权无碍。……凡国不相依附,平行会盟者,则于其主权无所碍也。”[9]而与此相反,半自主之国,即“惟立约恃他国保其事、主其议、护其疆等款,皆按盟约章程,以定其主权之限制。”由此可见,只有主权国家才完全平等,才可以通过条约、国际惯例等国际法关系获得权利、义务。而半自主之国的因其主权不完整而令其在国际法中的权利、义务受到限制。
而且,《万国公法》中还规定,主权国家的存在形式有两种,即独立或合并,即“邦国或系独立,或系数邦联合,以同奉一君相合者有之,以会盟而相合者有之。”[10]而主权国家的合并方式也存在两种,“相合而不失其内在主权:盖其内事,各邦虽自行主权,其外事并君位,则主权合二为一也。……相合而不失其内外之主权,其君位统一,其制法之会亦归于一,但各国扔有己之律法,己之理治也。各国之主权,无论行于内者行于外者,皆归于统一之国也。”[11]进而承认了一国吞并另外一国的正当性并为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由此可见,万国公法所描绘的国际秩序以条约体制为核心,它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主权国家通过签订条约的方式或独立进行国际交流、或进行合并,以强国吞并弱国的方式令弱国丧失部分主权而达到国际秩序的平衡。这样的国际观在幕末伴随坚船利炮传入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被日本利用,竟然成为它利用武力征服周边各国的有利工具。
二、日朝关系:传统朝贡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的竞争
万国公法原则上成为明治政府的指导思想,1871年岩仓使节团因为修约而出使欧美即是明治政府以万国公法为蓝本与西洋进行国际交涉最初步、最隆重的盛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操作中,毋庸置疑,日本对待西洋的国际交往态势完全是万国公法式的,但是它最初对朝鲜的交往却并非如此,而是沿用了幕府时期的朝贡体制模式。
1869年5月13日外务官向对马藩藩主宗义达发出对朝关系指令,命令其“一、对朝关系的大小事务要不时汇报,任命熟悉朝鲜国内部事务的官员两三名常驻东京以供咨询;二、做好对于朝鲜官职以及其他制度文书的整理和调查工作;三、对于朝鲜文物、地产和对日贸易上的问题提出建议;四、举荐对朝鲜国熟悉之人才以供不时之需。”[12]它标志着明治政府对朝鲜关系的重新确认,决定收回原本在幕府时期属于对马藩的对朝外交权,取代以中央政府对朝的全权外交,在实际运作中却仍然延续了幕末时期的朝贡体制。
1869年10月,明治政府采用幕末传统的文书格式向朝鲜发送了通知自国“王政复古”的《先问书契》和《大修大差使书契》,其中违反了对马藩与朝鲜国常用的文书格式,被朝鲜视为违反前例,进而拒绝受理。[13]
但是,对于采取传统朝贡体制对朝外交并非获得了外务省所有人员的支持,10月29日,外务省权少丞宫本小一郎的《朝鲜论》中则体现了其以万国公法为导向与朝鲜签订近代条约的外交倾向,体现了明治初年日朝关系中传统朝贡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的竞争,代表着外务省对于日朝条约体制建立的指针。
三、宫本小一郎《朝鲜论》:日朝条约体制建立的指针
《朝鲜论》中,宫本否定了幕府朝贡体制的日朝关系,认为委托对马藩与朝鲜交往的惯例“俨然变成宗家之私交”,在“御政一新之今日,与邻国之谊应另当别论,以正名义,应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交往,……不可再倡导因循古例、墨守成规之私例。”[14]他认为在“全世界文明开化之时势下,”不应“以暧昧之私交”、而应“以公法维持”交往。在此,宫本为日朝问题的解决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即利用万国公法、而非朝贡体制维持日朝关系。
理论上,宫本通过分析朝鲜国家之主权归属认为朝鲜的主权具有特殊性,即“朝鲜之国体极其暧昧,清朝大举讨伐朝鲜,朝鲜王面缚以降称臣,其君臣关系分明。但礼仪制度等百事却不受清朝之管辖,两国亦无直接痛痒之关系,外国人不将朝鲜视为清朝内部的属国。”故尔得出结论,“按西洋公法独立国与半独立国论之,朝鲜之主权属于半独立国。”再以西洋国体与主权论之,清国与朝鲜之关系乃“本国与属国的关系”。[15]
现实上,宫本认为,朝鲜不具备与西洋各国同等的国际法地位。因为,“万国公法上半独立国的使节无法获得与强大国家使节同等的对待,”再加上历史上朝鲜“与旧幕府交际之道极为繁琐和慎重,”甚至复杂到连今日日本与西方使节的交往亦无法比拟。若双方互派使节,朝鲜方则会因循繁复的旧例、日本参照国际法,因国际交往价值体系的不同令双方生出间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论及清朝与朝鲜的属国关系对吞并朝鲜的影响时,宫本认为,根据万国公法,“当属国与他国兴战争、起兵端之时,若藩国认定本国与属国战争无关、不派援兵、与属国不睦,则被认定为切断与属国之联系,他国则视属国为独立之国。”[16]而且,“方今西洋各国文明开化,……地球上因蒸汽船而产生一大变革,中国因不重视而受到万国之轻蔑,不足以信赖。难保朝鲜不会因为一朝事发而成为独立之国,难保宗社。”[17]也就是说,宫本认为,清朝和朝鲜虽然暂时身为藩国与属国,但是在文明开化清朝国力渐衰的背景下,难保在国际纷争引发战争之际清朝会出兵援助朝鲜,倘若清朝拒绝出兵,在万国公法上也就被视为自动放弃藩国的地位,自此朝鲜则会获得完全独立,日本则可以趁此机会吞并朝鲜,“成为兄弟之国,并为合众联邦。即朝鲜与日本缔结条约后则不与他国缔约。日本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引导决定与西洋通信交际之事宜,”[18]获得朝鲜的对外主权,至于甚至部分对内主权,对其进行“正朔年号、刑法、货币”改革。
四、明初日朝关系: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过渡
综上所述,幕末明初,万国公法传入日本,日本引入了近代条约体制的原则和价值观念。明治维新后,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日本无疑采用象征着近代性的国际法体系,但是其在处理对东亚的外交方面、特别是对待朝鲜的问题上却面临着两重文化价值、两套国际关系的抉择,即东方的传统朝贡体制和西方国际法体制的调和、冲突问题。
江户时代,朝鲜作为日本对外交往的两个通信国之一,日朝一直沿用中国传统的文书体制,即书契制度,其中以儒家礼法为中心严格规定了两国文书的格式,在“事大交邻”的原则下,隐含着奉中国为天朝、正统,日韩两国平等交往的含义。但是,此一传统的朝贡体制下的交往模式作为日本江户时代大君外交的代表,与西方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而逐渐形成的国际法体系形成严重的冲突。
明治维新的日朝关系特别是宫本小一的《朝鲜论》则显示出了此传统文书制度向国际法条约体制的过渡,此过渡代表着日本开始尝试以万国公法为蓝本重新解释日朝关系甚至清朝与朝鲜关系,而且其中隐含着对朝鲜半独立国身份的轻视和吞并朝鲜的巨大野心。
[1] 尾佐竹猛:《国際法より観たる幕末外交物語》,东京:文化生研究会,1930年,第1页。
[2] 同上,第127页。
[3] 山内进:《明治国家における“文明”と国際法》,一桥论丛,1996年1月,第19页。
[4]尾佐竹猛:《国際法より観たる幕末外交物語》,东京:文化生研究会,1930年,第1页。
[5]山内进:《明治国家における“文明”と国際法》,一桥论丛,1996年1月,第19页。
[6]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第224页。
[7] 穗积陈重:《法窓夜話》,东京:有婓阁,1916年,第174页。
[8] 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9-30页。
[9] 同上,第35-36页。
[10] 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1] 同上,第40页。
[12] 《日本外交文書》,外务省编,第二卷第一册,东京:日本外交文书颁布会,1964年,第856页。
[13] 参见王明星:《日本近代“征韩外交”再探》,《朝鲜·韩国历史研究》 2009年00期,第1-25页。
[14] 《日本外交文書》,外务省编,第二卷第二册,东京:日本外交文书颁布会,1964年,第855页。
[15] 同上,第861页。
[16] 同上,第861页。
[17] 同上,第863页。
[18]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