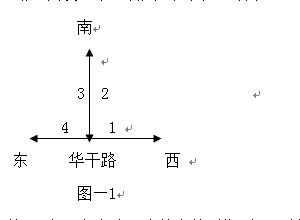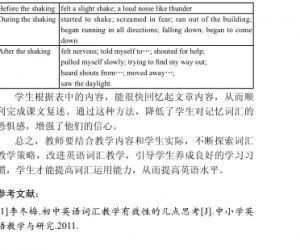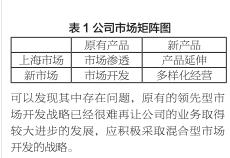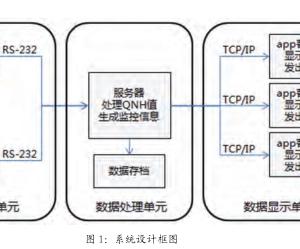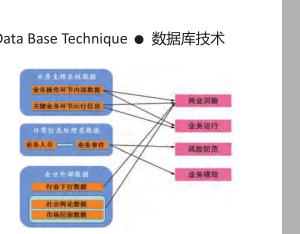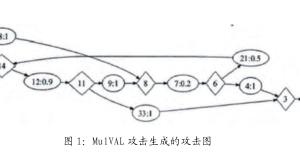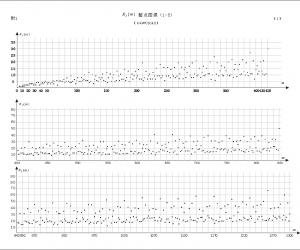自由文学理念的强势播扬——从《益世报•文学周刊》论析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观
论文关键词:人性;阶级性;创作自由
论文摘要:粱实秋在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期间,曾以多个笔名包揽了副刊的大部分文章,主要围绕着人性、阶级性、创作自由等问题展开,从中显示了离开论战中心上海之后,梁实秋对自己文学思想的集中整理和强势播扬,对文学本体建设和文学的自由发展都作了有益的探索。
《益世报》1915年由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雷鸣远创办于天津,至1949年天津解放停刊,“是中国近现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重要报纸,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旧中国四大报”。1932年正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受《益世报》主笔罗隆基的邀请遥编副刊《文学周刊》,从1932年11月5日至1933年12月30日止,每周一期,共出版57期,1934年梁实秋离开青岛赴北平任教,他在《益世报》的编务工作暂告一段落。这是一份以文化水平较高、以更专业化的受众为对象的文学副刊,以评论为主,学理性比较强。梁实秋此时刚及而立之年,正是年富力强且思想日渐成熟的时候,而上海的《新月》月刊已经式微,主编《文学周刊》为他全面阐释自已的文学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同时远离了文化论争中心上海,论战的硝烟也渐渐散去,正是梁实秋以沉静之心整理自己思想的重要时期,副刊大多数文章由他自己所写,计有100多篇,是一次对自己思想与观点的集中阐发与强势播扬。
一
梁实秋自由主义文学观的核心理念是“人性论”,它联系着梁实秋对文学的本质、价值、功能等问题的认识,他不但以人性为标准横扫新文学“浪漫的混乱”,而且在多篇文学批评中强调人性的观点。从《文学周刊》第一期就开始发表的《文学论》是一篇概述文坛的综合性文论,也可以说是梁实秋文学观念的总纲,全文分8期连载完,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总结,又有对新文学的检阅,既有对中国文学脱离人生倾向的批判,又有对过于功利的文学的讥讽,而他认为最健全文学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以人性为核心的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者,一方面注重现实的生活,不涉玄渺神奇的境界;一方面又注重人性的修养,推崇理性与‘伦理的想象’,反对过度的自然主义。”这一主张起码蕴含了两个基本点,一是文学要表现现实人生中的人性,一是这人性应是理性的和伦理的。
梁实秋认为,“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的描写”,“伟大之文学家能洞悉人生的奥秘,能彻悟人性之最基本的所在,所以文学作品之是否伟大,要看它所表现的人性是否深刻真实。文学的任务即在于表现人性,使读者能深刻的了解人生之意义”。伟大的诗歌,内容是人性的描写”,小说、戏剧、散文等其他文体也是如此,永久的共同的人性是文学的最佳选择,只有表现了这种常态的人性,文学才有价值,才会永久。在梁实秋的文学观中,人性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也成为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准绳,在《古典文学的意义》一文中,他认为真正的古典主义是在追求文学的普遍人性内容,而不是一个以时间来划分的概念,他以人性论重新界定了古典文学,认为《诗经》中能称为古典文学的只是一小部分,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也不是古典文学,古典文学决不是浩如烟海而是少而又少。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他也把人性看作是一把贯通古今的钥匙,“人类所共同有的情感如喜怒哀乐之类,人类所共同有的道德观念如勇敢慈善信义,反面的如对于欺骗谎语的排斥,这一切曾不断地在文艺里表现出来,古今初无二致。所以我们划分文艺的时代,自然不免要特别偏重各时代文艺的差别,然亦不可只看见‘异’,而忽视了‘同’,这是很重要的”,一切变动之中,人性是不会改变的。
梁实秋反复强调的人性与五四文学张扬的人性不同,五四时期张扬的人性大多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肯定人的感情欲求和自然本性,以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为内涵,周作人曾以《人的文学》为新文学运动奠基,胡适曾表述过自己的文学理想是“要有点儿人气、要有点儿人格,要有人味的,人的文学”,两位五四新文学的创建者所主张的人的文学,带有批判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建设意义,张扬自然人性的释放和人道主义精神。梁实秋的人性概念深受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有两个要点,一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表现人性,二是尊祟理性,“白壁德永远的在强调人性的二元,那即是说,人性包括着欲念和理智”。“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以理智控制欲念,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可以说完全继承了白壁德的衣钵,他的主要观点都能在白壁德那里找到源头。站在中西文化之间,伦理理性又使他找到了新人文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强调人性接受理性的指导,理性对个人的冲动和欲望加以内在的控制,和谐标准的人性只是在理性的生活里方能实现,常态的人性与理性的节制相结合,才能产生健康尊严的文学,才能产生伦理的效果。梁实秋是从建构文学本体出发而不是作为启蒙文化思潮来倡导人性的,也正是站在理性的制高点上,他不但与五四初期所倡导的“人性”相区别,对于同属自由主义思潮的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也大加挞伐。
梁实秋在这一时期的文章里,从新诗、散文的艺术讲到现代小说和戏剧的问题,从研究文学的方法讲到文学批评的标准,从反对浪漫主义到阐释古典主义的意义,人性问题是他论述文学的前提与基石。那么他人性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就他的表述来看不是指喜怒哀乐的情感现象,而是一种情感本质,“为作公债失败而悲哀,与恋爱悲哀,自然是不同的。其不同在悲哀的缘由,至于悲哀的本质,却没有什么不同,可见梁实秋虽然将人性归结为永久不变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却排斥情感的社会内涵,而是强调不关涉具体内容的情感本质,或者说是越过现象世界的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讲的“真”和“理想”。但人性毕竟是个抽象的概念,梁实秋在具体论述中有时等同于理性,有时认为是喜怒哀乐的情感,有时排斥自然人性,有时又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杂揉在一起,“梁实秋没有进一步阐述他整个文学理论中作为基石的‘人性’概念,这个概念对于他,就像现在对我们和对20年代及以后时期的中国批评家一样,无疑都是难以解释的“自在之物”。
梁实秋以人性为基础,对五四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和功利主义文艺观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描写人性,文学的价值在于陶冶性格、净化情感,完全脱离现实人生的浪漫主义是不可取的,而文学又不能与现实政治离得过近,失去文学的意义。他认为,强调文学的道德伦理功能,既能发挥文学干预人生的社会作用,又可避免急功近利地对现实直接参与,因此,他在功利派和超脱派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角度,即对人进行伦理自觉的培养和做人方式的指导,这种既主张艺术相对独立,又强调实际意义的文艺价值观,典型地表现了梁实秋自由主义的文艺态度。梁实秋的人性论思想是在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之外建构的,他的文学主张“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最早的标本”。他的人性论立足于文学本体,追求文学的本真与纯粹,致力于健全人格的培植和人的内在品性的修养,强调文学作用于人的根本目的以及它在形成人的观念和态度中的影响,带有超功利的性质。他试图以人性的标准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一条康庄大道,在时代对文学提出功利要求的背景下,执著坚守、特立独行,为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作了有益的探索。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探索与努力应该是文学这一广阔空间中的自由之声。但是,他所立足的人性是先验的抽象的人性,限制了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的容量,过分强调理性,也容易造成文学作品的拘谨。
二
当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时候,梁实秋感到迫切需要辨明的已不再是文学注重情感还是理性以及新文学的弊端问题,而是文学到底是表现人性还是阶级性的问题。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他认为文学应该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实现文学表现健康、优美、常态的人性,在《文学论》中,梁实秋认为文学的任务是“于森罗万象的生活状况中去寻索其潜在的人性的动因”“文学不能救国,更不能御侮,惟健全的文学能陶冶健全的性格,使人养成正视生活之态度,使人对人之间得同情谅解之联系”。在以编者身份回答读者来信时,他多次宣传自己的主张:文学不能救国,更不是宣传,健全的文学只能陶冶人的健全的性情,因此不要把文学与阶级联系在一起。
从文学本体出发,梁实秋认为文学无阶级性。他认为文学是独立的、普遍的,而不是某个阶级的,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差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的口号标语。从创作主体看,一个文学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失掉独立的地位,作家的创作与所属阶级无关,“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上没有多大分别”。“强分作家为两个阶级,或左右二翼,这对于文学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利益”;从作品来看,“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从读者来看,无产者有能欣赏文学的,有产者也尽有与文学无缘的,讨论文学问题,应该把把经济的阶级的观念抛开,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观察。他在《文学周刊》第六期翻译了马克思的作品《莎士比亚论金钱》,在第八期撰写了《马克思与诗人》,通过马克思喜爱诵读歌德、海涅、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意在说明无产阶级领袖并不拒绝布尔乔亚文艺,“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出了一种主义一种运动之创始者与领导者,和他们的盲从的徒众,其间有多么大的分别。领导者的态度往往是开明的,而盲从者的态度往往是愚暗而态肆”;从文学批评来看,“单是阶级性并不能确定一作家或作品的意识与艺术,至少民族性遗传性教育训练等等也是形成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之不可避免的因子。所以确定阶级性只能成为背景研究之一部分,也可说是批评工作之初步的准备之一部分”,真正的批评还是要发挥作品中的人性。如果说梁实秋最初提出人性论是为五四文学纠偏的话,那么在与普罗文学论战的时候,人性就是其否定阶级性的武器。
在《文学周刊》上,梁实秋除从理论上为自己的文学观念铸造基石外,还尤其关注左翼理论著作,他批评了谭工模的《新兴文学概论》,撰写了长篇文论《普列汉诺夫及其艺术理论》,意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不少武断的地方,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译著多有攻击。对于左翼作家的作品,他也及时做出批评,否定左翼作家的作品,比如《鲁迅的新著》、《两地书》、《关于张天翼的小说》等。为了让读者认识无产阶级文学,他还在自己的刊物上登载了一些普罗文学作品。这样做,充分显示了梁实秋对自己文学观念的自信和执着。
然而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入以及对文坛论战的反思,《文学周刊》时期,梁实秋对阶级性的理解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阶级斗争既已由理论而成为实际活动,那么斗争在文学里得到反映也是自然的。但是若说文学必要以斗争为题材,这便可议”。他开始承认文学创作可以写一些阶级斗争,但反对把阶级性作为惟一题材,反对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生活的全部。他也认为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并存,“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现之别”,文学仅仅是可以写阶级斗争,但文学的价值在于人性描写的部分,而不在于阶级性表现的部分。这些观点与以前他的文学无阶级性观点相比,已经趋于辩证,因为阶级性与人性并不是完全对立关系,从外延上来讲,人性应该包括阶级性,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阶级的出现,造成不同的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对立有冲突,但在人类的生存过程中,除了这些方面外,还有一些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欲求,阶级性不是惟一的,这些都应该是文学表现的内容。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复杂环境中,梁实秋大讲文学的普遍人性,不趋时、不附和,体现出坚守文学品格的一些追求,对普罗文学中过分强调阶级性确实是个有益的补充与调节,对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给予及时地思考与判断。3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无产阶级阵营需要文学反映本阶级火热的斗争生活,需要文学为本阶级利益服务,从当时的革命需要这一特定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文学为政治服务,很容易使文学偏离文学正常发展的轨道,比如政治高于艺术、思想大于形象、主题先行、概念化、公式化等,对文学自身的发展非常不利,也限制了文学应有的活力。对于普罗文学出现的一些间题,处于激情澎湃中的普罗文学家们不可能冷静理性地思索。梁实秋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看到文艺思想领域的偏激之处,指出了政治思想对文艺最初的兼并,应该说有可取的成分,但人性论视角也使他看不到左翼文学的特殊价值及时代合理性,并以人性论对抗阶级论。与《新月》时的疲于应战不同,《文学周刊》时期梁实秋往往是主动出击,针对以前与左翼文学论争的老间题进行辩白和发难,对鲁迅这样一位自己的宿敌自然不会例外。或许是因为远离了论战的中心,与上海时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以致产生了大量论战文章相反,这时很少看到左翼文学包括鲁迅的直接回应。
三
梁实秋对人性、阶级性的认识,使他试图消解文学的工具论,而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作家主体来讲,他认为创作的自由是产生有价值文学的前提。创作自由是其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受英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他不愿意从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不主张激进的方式,也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社会地位和文化倾向决定了他把自由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与现实人生直接联系的价值目标,自由主义思想投射到文学价值观方面,就是追求不受任何势力所左右的创作自由。
梁实秋建立在思想自由基础上的创作自由不是针对哪个政党哪个阶级的,而是一种自由的文学意识。在30年代特定的时代环境下,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学运动中,普罗文学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学,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但因两派关注的都是文学的直接政治作用,这与梁实秋的文学本体观相去甚远。梁实秋承认文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但在理解这种关系时强调不应该把文学当作宣传工具,因此,他对国民党用三民主义文学统一文艺大加讥讽,对普罗文学的强调阶级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他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自足性,不应该沦为任何一个阶级的宣传工具,否则,是无法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学来的。他的主张对左翼文学和国民党的御用文学都形成有力的冲击。
梁实秋对于普罗文学以文学为革命的宣传十分不满,反对把文学当作“武器”,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他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强调是先有文学,后有主义,不能先有主义,后有文学,“如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以文学为政治的宣传,干脆说,这便失了文学的立场”,文学是文学,宣传是宣传。退一步讲,“我们不反对任谁利用文学作工具,但是我们不愿任谁武断地、只承认如此方是文学”。在他看来,具有永久性的文学必须表现生活的常态,而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变态,不是常态的生活,“无论如何,文学家是并不听命于理论家,批评家,或革命的宣传家的”,宣传主义是一件事,欣赏文学又是一件事,所以屠场、铁流与哈姆雷特、失乐园,将各有各的读众。文学家什么时候都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都应该保持独立的个性、自由的人格,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写出人性的文学,才能维护文学的独立与纯正。
针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梁实秋的批评也相当尖锐。当他看到左翼文学的宣传性与工具性的时候,他批判左翼文学;当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对左翼文学绞杀的时候,他也强烈地抗议, “对于真正爱好文学的人,文坛生添出了一批普罗文学,这是该加欢迎的事”。“普罗文学的理论,是有不健全的地方,本刊屡有批评,可是他的理论并非全盘错误,实在它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艺术论有许多点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并且是文艺批评家所不容忽视的新贡献。即使反对普罗文学的人也该虚心地去了解它,然后才能有公正的判断”。梁实秋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左翼文学生出很大的同情,并表示这不是示惠于人或故作公正,而是不符合思想自由文化自由的原则,“凡赞成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的人,对于暴力(无论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对的”。他认为,思想是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的,思想只对理智负责,对真理负责,反对任何党派任何阶级对思想言论的钳制,维护创作的自由。
梁实秋之所以既批判普罗文学,也批判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显示出独立超然的价值取向,是因为他从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出发,主张文学的独立性和多元化,反对在文学上强调思想统一,不管是哪一种文学,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站在一个自由主义立场上,只要他们限制了文学的发展,他都有可能反对,也因此曾受到来自左翼右翼两派文学的抨击。他反对的是对文学本质认识上的偏差。梁实秋说他终生信服伏尔泰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在现代文学时期,梁实秋的创作自由论与很多自由主义者取得认同。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强调,“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指导”。从胡适到沈从文,从“新月派”、“论语派”到“自由人”“第三种人”,都发出过创作自由的要求、从文学的独立性出发,从建设文学本体出发,要求解放创作主体,追求文学的超功利价值。梁实秋的创作自由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梁实秋从文学的现代化建设角度,在阶级斗争、民族救亡的激烈环境中,张扬创作自由,为3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有他这样的作家的坚守,文学才成为多色调多音部的存在,他的文学观念也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从五四开始,自由主义文学一直倔强地生长,只不过在如火如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文学与其他文学主张结成思想同盟,对抗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体现出文学战线的统一性。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社会变革和文学变革双重使命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要变革社会以图民族振兴,另一方面要建设新文学以图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由于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文学的现代化建设还没有充分展开,就被淹没在社会变革和民族救亡的疾风暴雨中。梁实秋主编《文学周刊》的30年代,不但新文化统一战线已经解体,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日益尖锐,文学生存的环境不同,自然对文学的定位就会发生变化。在这一文化语境下,梁实秋既高扬自由文学的大旗,又以古典主义的和谐均衡来节制自由,显然是与时代错位的,不合时宜的,其自由主义文学观也会遭到反击。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纯粹的文学立场,从文学的发展规律与发展远景来看,却有着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