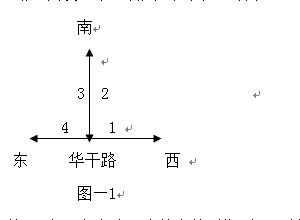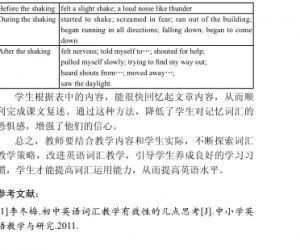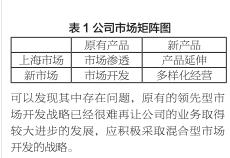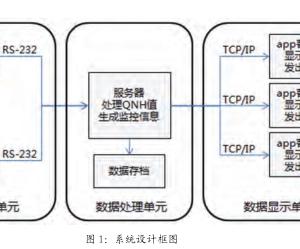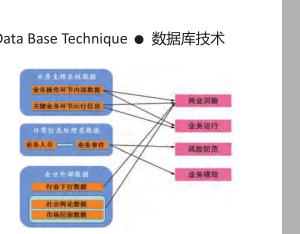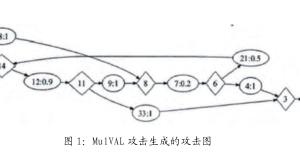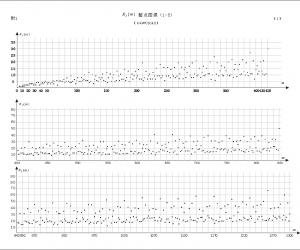作为文化的传播——詹姆斯凯瑞和他的传播仪式观概览浅析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发布者:lunwenchina
热度0票 浏览364次
时间:2020年10月21日 14:21
郝凌宇 / 中国传媒大学
摘 要:詹姆斯·凯瑞是现当代美国较为著名的传播学者之一,作为传播学者,他所提出发展的传播仪式观享誉全球,很多学者在这一理论启发下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为传播学研究做了不少补足。本文试图通过对凯瑞的观点形成过程进行复盘,以历史的视角还原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传播仪式观;传播学;詹姆斯·凯瑞
詹姆斯·凯瑞 (James Carey,1935-2006), 曾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Urbana-Champaign)传播学院院长,1992 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还曾担任过美国《传播》杂志的主编以及美国新闻记者协会主席。作为文化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communication)为美国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涉猎传播学研究领域,此时美国的主流传播学研究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开创的效果研究模式。凯瑞对此种研究模式十分不满,他认为,这样裹足不前的研究毫无意义,“应该从生物学、神学、人类学及文学中的一些知识材料中另辟蹊径,以免像现在一样原地打转”。由此,凯瑞认为应当从重新认识什么是传播学入手,才能建构起一套不同于实用主义传播研究的新的路径。
一、思想源流及阐释
在解读传播的定义时,凯瑞最先想到的是芝加哥学派以及约翰杜威。 杜威认为,要将工业创造的大社会改造成一个大共同体,如何构建共同社区共同集体认同,大众传媒讲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凯瑞不仅继承了杜威这个观点,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将杜威看作是芝加哥学派的起点和核心。他从杜威名言“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存在,更确切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入手,向我们介绍了两种在他看来二元对立的传播观: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凯瑞认为,在传播的传递观下,传播被理解成为传送,指的是“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这种传递观下的传播研究在凯利看来过于强调实用主义,具有过强的功利性。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communication)则是将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传播应当是一个文化共享的过程,传播学研究应集中在如何更好的实现“让社会保持一致”的目的。凯瑞认为传递观的局限在于错误的将传播的传递性特征当成了本质,而忽略了传播的文化层面的意义,他还在《芝加哥学派与大众传播历史》一文中,给出了美国大众传播起源的另一种解释:在美国这个新兴的移民国家中缺乏一种共同的继承文化,这样传播就必须承担起社会整合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把社区组织起来的唯一方式是通过讨论、协商与传播。在凯瑞看来,这一阶段的传播在社会整合巩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和研究价值。
同样的,哈罗德英尼斯对于凯瑞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英尼斯认为人类媒介的演变历史是从偏倚时间的传播媒介向偏倚空间的传播媒介发展的。偏倚时间的媒介如泥板石碑等不具备快速扩散的特性,所以适用于范围较小的社会;而偏倚空间的媒介(如电报或者电视)虽然能够及时且迅速扩散到极大空间的范围,但实质上却不利于信息和传统的继承,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这种二分法,基本上复制了英尼斯有关媒介——社会的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的二分法。
除了以上两位学者,凯瑞在自己行文的时候还提到了韦伯(Max Webber)、涂尔干(Emile Durkheim)、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一大批社会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如此做是为了在传播学研究中引入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中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这一点与当时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所倡导的实证的研究也是大相径庭的。郭建斌在梳理了文化研究的知识图景之后,为了更好辨识凯瑞所倡导的文化研究,将以往研究主要区分为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基于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
他认为凯瑞最终“从方法上打通了英国文化研究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之间的联系”,具有更强的文化人类学色彩。这一点胡翼青也在 2014 年的文章中表示了赞同,但是对于凯瑞如此做法的合理性却产生了质疑。
二、对于传播仪式观下文化研究的思考
传播仪式观的提出,对于凯瑞自己而言就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实证研究,所以他自己除了在理论上力图重新界定传播的概念以及美国传播学研究源头之外,还努力在传播学研究中推崇文化研究。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曾经也提到了传播学研究的三种策略,传播学被分别作为行为科学、正规科学和文化科学来进行研究,其研究方法也对应为对规律、结构和意义的研究。凯瑞认为应该抛开预测人的行为反应,着重来研究人的行为本身。也就是说,传播仪式观并不在乎传播给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或者功能,而是关注传播究竟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的角色。传播过程是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或使用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凯瑞并不试图给传播过程中人们的接收、反馈以及可能的改变或者其他行为做出预测判断和评价,而是追求理解人的行为本身。“文化研究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的意义。在更积极地方面,它绕过了行为研究所看重的经验主义与正规理论空中楼阁式的玩意儿,并深深扎根于经验世界中。”
对比实用主义的传播的传递观所采取的实证研究、量化研究,传播仪式观当中的文化研究又应当采取何种研究方法?
对此凯瑞提到了阐释的研究方法。阐释的想法来源于凯瑞对于格尔兹理念的解读。格尔兹认为“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传播中所有的媒介(如电视,电影,书籍)都是人类传播行为的一部分,研究应当抛开这些孤立的结构性的元素研究而着眼于人类传播行为本身。凯瑞把这个行为看成是一个文本,文本本身包含许多符号,在传播仪式观下的文化研究要做的工作就是在独特语境下对不同的“文本”进行解读。这种倡议在当时的美国传播学界看来无疑是离经叛道的。
胡翼青在凯瑞的“仪式观”: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困局一文中,通过对学术史料梳理,最终得出结论:凯瑞所谈的文化研究只是个方法论层面的文化研究,不是一个丰满的理论体系,而且也很难依照她的设想开展传播研究。凯瑞在提出这套方法论后并没能进行任何一项研究,这种框架也没能说服学术同仁对于传播文化研究这个框架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