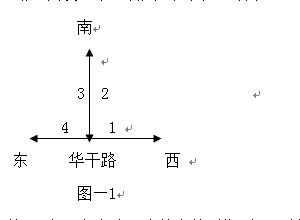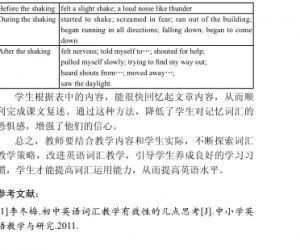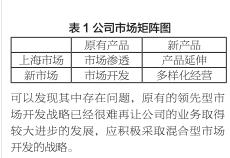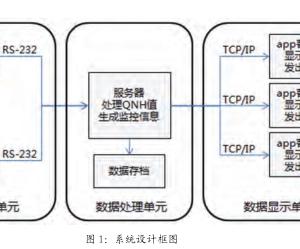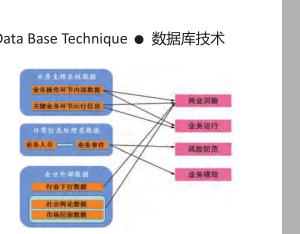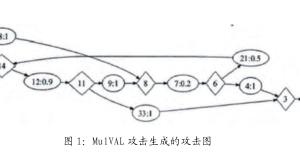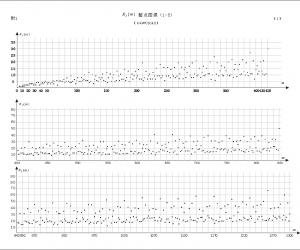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之检视——以司法方法论为视角
【摘要】在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法官职业化可谓是一个至关重要但却“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学理上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丰富而翔实,但时至今日也仍存争论;司法实务中,践行法官职业化的举措和改革纷至沓来,但也未能最终形成严实而精良的规范。法官职业化是法治发展的趋势和必然,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潮中,必须严格、严谨而严肃地对待法官职业化之诸多问题。本文拟从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进行论述,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我国法官职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法官职业化;司法方法论;同质化
法官的非职业化是我国司法的痼疾之一。从司法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和探讨法官职业化的相关问题,对夯实我国法治进程的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一 、法官职业化的发展源流
作为一种制度,法律职业化始于13世纪的英国。韦伯指出:“对于职业性法律训练以及在这种训练中的特殊法律思想类型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将法律作为工艺的经验性训练路线,这是一种在法律实践中师徒的训练方式。第二种是在特殊的法律学校里教授法律,按照这种方式,重点是法律理论和科学,即以理性和系统的方式分析法律现象”[1]法官作为一种独特的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愈加精确及严密而逐渐从职业体系中剥离出来。
职业化要求专门从事某类工作的人们形成独特的知识、技能、方法、生活方式及思维模式。法官职业是通过法律的适用这一中介环节,把法律规范的抽象设定和普遍要求,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具体单个的行为。[2]首先,“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言说的知识,一套自恰、不矛盾的例题,一套可以演绎成篇的逻辑,而且是一种话语的实践,一种对参与者的训练。”[3]法律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属性及技术性,这必然要求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官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其次,“法官适用法律依靠于自己对法律的解释,每个法官都带着自己的‘视界’,‘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但‘每一种视界都对应于一种判断体系’”[4]。法官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不仅仅是停留在分析案件事实,解释运用法律这些具体而实际的“形而下”的范畴之内,也常常会上升到法律是什么,司法功能、司法与立法相互作用的层面上来。司法活动过程也与法官所持的政治、经济哲学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另一位优秀的美国法官汉德所说的“对一名被要求审核一个有关宪法的问题的法官,他除了要熟悉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著,还要懂得一点阿克顿和梅特兰、修昔底德、吉本和卡莱尔、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马基雅弗利、柏拉图、培根、休谟和康德。因为在这些知识中,每一种都全有助于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5]法哲学思想使得法官职业成为一个有着法律文化氛围的独特职业,也使得法官有着睿智的眼光、敏锐的判断力和对法理的深刻洞察力。
二、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
方法论问题是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自身的反思与审视的结果。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提到“方法论的自治性是其所谓的‘法律秩序’之重要特征”。[6]基于独特的方法论基础上法官职业的职业化有着必然性及必要性。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逻辑推理
有如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所谈到的“法律推理具有一种使其区别于其他科学解释以及伦理、政治、经济论证的方法或风格。”[7]现代司法是以理性推理为特征的。即以法律和事实两个已知的前提,运用科学的方法和规则为法律适用提供正当理由的一种逻辑思维活动。按照法律形式主义的理想模式构建的司法系统是一个巨大的三段论机器。只要一个具体案件事实满足某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要件,则可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相应的结果。法官的角色似乎只是技术熟练的机械工人,只需其正确识别外部规则。且由于法律推理乃直接自既定规则出发,无须触及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价值判断如正义等问题。[8]法官的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获得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逻辑关系进行内心确信——形成判决的思维推理过程”。这种无限往复的逻辑推理过程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并逐渐外化为一种定向的思维习惯。
(二)经验总结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并没有给予经验一个准确的内涵和外延,但其并不是要向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可供套用的规则,而是要使司法过程由逻辑推理转向社会政策考量,由机械适用法律教条转向灵活应对社会问题,由法律内部因素的“画地为牢”转向外部社会因素的“统筹兼顾”,由追求形式性的一般正义转向追求实质性个案正义。[9]
案件的多元化与个案具有的惟一性特征决定了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要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联系,这要求法官在长期的职业活动中不断的总结经验并加以验证。在裁判过程中,考虑的对象不仅是客观法律事实本身,而应将法理、情理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这项技能需要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长时间的积淀。可以这样说,每一份判决都是一个法官的职业经验与人生阅历在法律裁判过程中的呈现。
(三)利益衡量
波斯纳指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未必会导致利欲熏心,它也可能使得一个职业追求良好的行为和“产品”。法官裁判的过程绝非简单地针对个案的现实特征、性质,选择相应的法律,加以套用。事实上,在错综复杂的具体事实面前,一个判决必须最大程度的实现法律的价值,达到最优化的利益效果。法官不仅要遵守实体法和程序规则,还必须进行利益衡量及选择。
所谓利益衡量,指的是法官查清案件事实后,不急于翻查法律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10]法官的裁决过程即为对比案情以及各种裁判所会达成的社会效果,择取最优化的裁判。
(四)法律解释
社会行为的不可预测,法律的制定过程中难免出现漏洞以及现时制定的法律并未能完全包涵将来出现的情况。如同艺术创作一样,法官的裁判也要紧随时代潮流,表现社会的新兴吁求,尤其是在既有法律规则已落后于社会发展时,应对其涵义做出“与时俱进的解释”。[11]这是司法活动保持其时代性的必然。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的原本含义以及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所作的探索而形成的解释,一般包括法律的本意解释和对法律的不足补充。基于自由裁量权的享有,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进行创造性的法律解释,有利于保障司法过程的顺利进行。但法律解释也绝非是为了冠冕堂皇地越轨而抹煞个案正义,而应秉承最大限度的体现立法本意,还原事实,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
三、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之检视
职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对一个职业的教育背景、技能训练、行为伦理、身份地位、等多方的合理制度构建及安排。法官职业化不仅要对法官队伍本身进行深度改造,还包含了对法官职业所处环境的良好期许。从司法方法论的视角对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进行检讨和反思不无裨益。
(一)法官选任应有所区别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法官选任标准仍然较低。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及其他简单条件,基本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职务仍不失为一种“福利待遇”被平均分配。不同层次的法官职业化标准不明确。事实上,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和要求,不同层级法院的法官应当各自偏重于某种素质,以适应不同层级法院所面对的案件和情况。
一名合格的法官当然应掌握独特的法律方法。如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难以想象的是,尚未养成独特方法论的人进入法院担任法官将会产生的后果,更遑论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最高人民法院。事实证明,非建立在合理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法官队伍,存在诸多问题,专业技能及职业操守中均是如此。忽视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评价和衡量法官的基本素质,将很难精英化。笔者认为,对基层法院而言,法官侧重于对个案细节的细研及大量、快捷的解决纠纷,所以对基础法院法官的选任应侧重于解决事实争议的能力和经验,要具备丰富的社会见解、清晰的洞察能力及高超的调判技巧,并适当关注其法学理论水平。基层法院案件量繁重,且处理同样数量案件的工作量要比上级法院的工作量大,对基础法院的法官员额应有所倾斜,以适应基层法院的司法任务需要。上级法院侧重于规则的制定及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其法官的选任应侧重于理论功底深厚、学术才能突出,善于从不同的案件事实中发掘清晰而准确的法学理念,并能够上升为一般性规则。
(二)同质化程度的提升
(三)继续教育的完善
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决定了法官应是一个理性的、独立的居中裁判者,法官具有天生的保守性。[12]法官职业化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职业性的封闭和保守。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化日新月异,与保守的法官职业存在紧张关系。保守的法官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司法的方法论能够不断的发展更新,法官的继续教育问题必须完善。
特别是对现任的、缺乏系统的法学教育的的法官,应集中组织、强化学习。他们通常有多年的办案经验,有着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通过继续教育,深化其法学理论功底,强化现代法律意识。对所有的在任法官,应分批、分流的“回炉”,通过继续教育,实现知识更新和理论提高。尤其应针对社会出现的新案例、新法律应重点加强、及时学习。
法官职业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方法论是对其进行反思和检讨的重要视角。法官职业化建设并非一人一力一时能够完成。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法官职业的教育背景、技能训练、行为伦理、身份地位、职务特权、组织构造等进行制度构建及安排,这不仅是法官职业内部一个渐进调整过程,也是法官职业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过程。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而言,法官职业化的真正实现必将开启新幕。
*程秀建(1982—),男,汉族,安徽滁州人,法学硕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员,从事房地产案件审判。
*万娟娟(1982—),女,汉族,湖南湘潭人,法学硕士,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法律学系讲师、系主任助理,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1]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版,第198页。
[2]公丕祥:《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3]梁治平:《法治进程中的知识转变》,载《读书》1998年第15期。
[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5]亨利•J•亚伯拉罕《法官与总统——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43页。
[6]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47页。
[7]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8]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9]秦策:《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载《法学论坛》2005第2期。
[10]梁彗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11]孔祥俊:《法律解释方法与判断研究》,人民法院出版2004年版,第14页。
[12]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