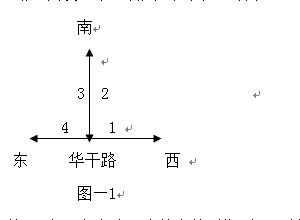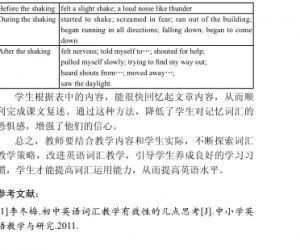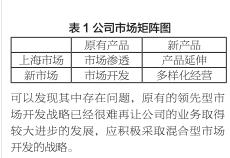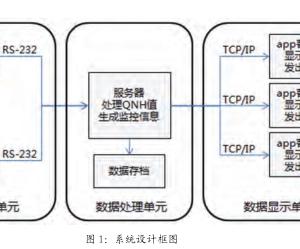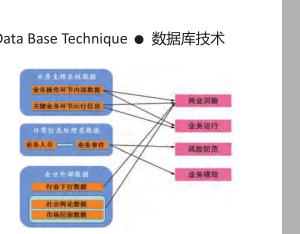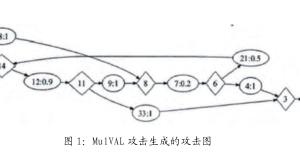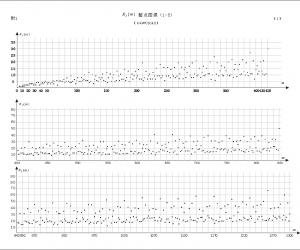中原作家群关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表达——乔叶和刘庆邦同题异构 小说艺术比较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发布者:lunwenchina
热度0票 浏览126次
时间:2020年7月23日 15:11
张凤梅 /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 要: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原作家群关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主题表达是比较常见的,但同一个文学主题,在不同作家那里呈现出的文学艺术也是不同的,刘庆邦笔下的煤矿工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群体备受关注,特殊的生存环境、特殊的社会身份、特殊的命运使他们不断地被“边缘化”,无法回归乡村却又无法融入城市。本文以刘庆邦的新作《红煤》为例,来解读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作家对煤矿工这一边缘群体命运沉浮的关注。
同时作为"70后"的主力作家之一,乔叶也注重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但她并未局限底层生活的苦难与艰辛的书写,而是着力透过苦难勘察人性的奥秘 , 表现人性的美好。因此她的作品超出了一般 " 乡下人进城 " 的叙事模式 , 把城乡的巨大差别投射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 表现农村人的身份焦虑、都市情结以及被都市接纳后的欢欣。这些作品克服了当下普遍存在的 " 苦难焦虑症 ", 触摸到了底层民众的灵魂世界 , 是值得予以讨论探究的。
关键词:乡下人 ; 进城 ; 同题异构 ; 小说艺术
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原作家群关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主题表达是比较常见的,但同一个文学主题,在不同作家那里呈现出的文学艺术也是不同的,刘庆邦笔下的煤矿工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群体备受关注,特殊的生存环境、特殊的社会身份、特殊的命运使他们不断地被“边缘化”,无法回归乡村却又无法融入城市。本文以刘庆邦的新作《红煤》
为例,来解读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作家对煤矿工这一边缘群体命运沉浮的关注。同时作为 "70 后 " 的主力作家之一 , 乔叶也注重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 , 但她并未局限底层生活的苦难与艰辛的书写 , 而是着力透过苦难勘察人性的奥秘 , 表现人性的美好。因此她的作品超出了一般 " 乡下人进城 " 的叙事模式 , 把城乡的巨大差别投射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 表现农村人的身份焦虑、都市情结以及被都市接纳后的欢欣。这些作品克服了当下普遍存在的 " 苦难焦虑症 ", 触摸到了底层民众的灵魂世界。
青年女作家乔叶以其清新的散文、富含哲学意味的小说在中国文坛上异峰突起,形成了继张爱玲、三毛、席慕蓉等强势女作家之后又一股席卷而来的女旋风。评论界称道乔叶为“文笔细腻独特,清新隽永,富有哲理和智慧,对生命和人生的意义有着深沉的思辨和探索,多样化的题材统摄在机敏的基调中,蕴藏着准确动人的知识内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乔叶的获鲁迅文学奖的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不仅题目耐人寻味,叙述风格自然脱俗,更重要的是在小说关于两代女性的性格冲突之讲述中,以毫无传奇的生活细节,塑造着生之深奥和生之伟大,乔叶用一个“慢”字概括着生命之渐次的演化、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冲撞与最终达成的和谐,于是“慢”就有了一种玄奥的内涵。
在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中,奶奶和二妞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的女性,奶奶显然是农业时代的女性,而二妞早已进入了工业时代。尽管这两种不同时代的女性早期生活在同一座宅院里,但不同的周边环境、不同的生活理念把她们无情地切分为两个世界里。因此,奶奶守旧而简朴,二妞乖张而放荡,奶奶生活在回忆里,二妞生活在幻想里,奶奶希望生活宁静不变,终生与土地为伍,二妞追求生活的多彩和刺激,在不断地变更男友中寻找快乐。然而这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都抵挡不住缓缓慢慢的时光,这两代毫无相同之处的女性最终在慢慢的时光里达成了一致:希望生活一成不变的奶奶最终进到了城市,接受了每天出入饭店、睡席梦思、洗热水浴、听交响乐的现代生活,而追求新鲜刺激的二妞却老老实实地嫁了人,在婆家相夫教子,在医院里伺侯生病的奶奶,活脱脱成了一个孝顺的女孩子。在无法的抵抗的时光之“慢”
中,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时代相融合了,两代女性都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又都在悄悄地和谐着对方。她们身上原有的芒锋都被“慢”所磨去了,她们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也是最适合于对方的生存状态。于是缓慢的生活呈现出的一种超乎寻常的宁静:“那些日子,我和姐姐在她身边的时间最久。
无论对她,对姐姐,还是对我,似乎只有这样才最无可厚非。
三个血缘相关的女人,在拥有各自漫长回忆的老宅里,为其中最年迈的那个女人送行,没有比这更自然也更合适的事了。”
而在奶奶去世之后,二妞却感到了和奶奶的亲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她可以在许多事情上看到奶奶影子,在许多细节上回忆起奶奶,在许多时刻感受到奶奶的存在,这说明奶奶已融入二妞的生命里,让她永远无法割去 : “在生命的感觉上,我却仿佛离她越来越近。我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见她,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看见她。她的一切细节都秘密地反刍在我的生活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奇袭而来,把我打个措手不及。”
“不止这些,我甚至觉得村庄里的每一个人,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她的孩子。
“文学总是要表现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矿工和大自然的抗争是最直接的,最严酷的。大自然造化了地球球体表面的万事万物,同时也造化了球体深部内容丰富变化莫测的世界。煤井下的采矿场就是这世界的一小部分。比之于地面,煤矿井下没有风霜雨雪,没有呼雷闪电,没有洪涝,也没有地震,可井下的瓦斯爆炸就是雷电,透水就是洪涝,冒顶就是地震,落大顶卷起的飓风就是横扫一切的台风……。”刘庆邦在《红煤》中并没有直接地为读者展示酷烈的井下生活场景,但从夏观煤矿和红煤村煤矿工所发生的冒顶、透水两次事故来看,不难看出矿工的生存形态和他们的命运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对矿工日常生活的展示,其实就是对一种生存形态的展示:强悍恣肆的灵魂、粗鄙的语言、残酷的复仇,险恶的环境……也正是这样一种环境更能彰显人类生命的脆弱性和命运的悲剧性。宋长玉为了改变自己命运,选择了“进城求生”的道路和生存方式,但这并不仅仅是宋长玉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千千万万“进城求生”的农民工的共同的选择。
作为生命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生存形态的权利,人生有许许多多的选择可能。但矿工的生存境况促使他们与普通的生存嫁接方式不同,在没有身份、地位、权力优势可言的这些生命群体身上,他们所选择的似是偶然,事实上,已经是唯一可选的答案了。“往外奔,其实一直是父辈们心中的宗教,是山咀子每一个人心中的宗教,一如街与道的宗教” (《街与道的宗教》),往外奔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的途径,在宋长玉眼里,在千千万万有着农民身份烙印的生命个体的眼里,“农村和城市是两重天地”,人为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社会身份的划分,使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神秘的“围城”, “城内”的文明与繁华和“城外”的愚昧与贫瘠,让生活在城外的人有着世世代代的“进城”的冲动,做着永远的“城市梦”。
但这种“城市”梦想的实现,在当下现代化的语境中对农民来说注定是一种痛苦的过程,刘庆邦笔下的矿工更不例外,到煤矿做一个煤矿工,摆脱农民的身份,这是他们对于生存形态做出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中蕴涵着悲剧的命运,“瓦斯爆炸、透水、冒顶”掌控着他们的命运选择。面对遭遇矿难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命运在自己手中失控。他们在选择一种生存形态的同时,也就选择了一种扑朔迷离的命运,下井和出井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生与死的较量,“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的命运”。这样的生存形态,不仅对生命提出了严酷的挑战,同时也暗含了命运的结局。人的命运有两个部分,一半在自己手里,一半在上帝手里,生命的过程就是用你手中掌握的一半去换取上帝手中的另一半,和命运抗争就是和自己抗争。对煤矿工人而言,他们心中的上帝又是什么样子,又存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如何用自己手里的一半去换取上帝手里的一半呢?刘庆邦笔下的煤矿工也许能给我们提供最好的答案。
在社会科学领域,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德国心理学家 K·勒温首先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性变动的概念亦能适用于个人社会心理的变化。社会地位的改变能使个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发生改变。当一个人从一个工作环境转到另一个工作环境时,以前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养成,还未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此时对于新的工作环境来说,他的所属性是不稳定的,因此产生紧张感、失落感,表现出过分小心、谨慎、自卑感和不敢自作主张,对自己的天性进行抑制等。这种人是处于两个群体的边缘人。他们行为表现是很特殊的。地位上升或下降、从乡村到城市或从城市到农村,移民等人都属于边缘人之列。
边缘人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整个过渡期间对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特别的影响。
他们没有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缺少固定的住所,他们只能靠出卖体力或者寻找一些不被城管承认的灰色工作,他们经常遭到城里人的白眼,他们忍辱负重地生活在社会的最边缘。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愿意离开城市。人们称他们是“城市边缘人”。 在中国,“农民”就是一种身份,这种身份的形成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户籍管理的体制下,把城市居民划入非农业户口,农民划入农业户口。由此,便形成了两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阶层,他们受到国家两种不同的待遇,彼此之间也以“城市人”、“乡下人”为区分,同时也根据所从事的职业的不同,有了“工人”、“农民”、“干部”身份的划分。这种农民的身份和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相对应的,他们往往处在“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最底层。
这种底层的社会地位和农民的身份往往成为他们自身命运的枷锁,在森严的城乡壁垒面前,农民有的只是相依为命的土地,对“城”是一种想象和向往。农民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是和土地紧紧相连的,土地就是农民拥有的资本,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也就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根本,他的命运也就象无根浮萍,注定是永远的漂泊不定。而这种城乡二元分割和社会身份的认同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农民在心理上的“进城情结”,城市代表着文明和美好,城市对他们充满着诱惑和魅力,使他们不顾一切地要冲进城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壁垒的打破,农民进城成了一种“潮流”,大批的农民开始涌向城市,所谓的“民工潮”
就是该时期这一现象的代名词。于是“农民工”作为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日益成长为一个迫切需要社会认可的新兴阶层。
这种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显得更为重要,它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同时也和命运的变紧密相连。在农民眼里,只有改变他们的社会身份,改变社会地位,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红煤》
中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宋长玉就出生在农村,这种“先天”
出生的空间因素决定了他的“乡下人”、“农民”身份和社会地位,在他的自我认同中,他就是农民,但重要的是他有着“城市”的梦想,为了能走出农村,彻底告别农村、农民、农身,实现做一个城市人的梦想,高考落榜后来到一家国有煤矿做轮换工,他不愿意轻易放弃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他渴望挣脱的是农村、是土地,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农村还有城市,城市在高处,农村在低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要想有出息,必须到城里去。”在宋长玉看来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道路就是“进城”,“向城求生”,做一个城市人,得到城市人的一种社会身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可以说是他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经过种种波折和努力,宋长玉从一个农民轮换工成为了红煤村煤矿的矿长,不但在城里买了自己的房子、车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了城市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这种身份的标志就是宋长玉有了城市户籍,他也就理所当然的可以成为城市“市民”,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梦寐以求的“象征资本”,社会地位也随之改变,成为拥有权力和资本的煤矿主。应该说宋长玉的命运从此将被改写。然而,他仍无法逃脱注定的悲剧命运。在小说结尾我们看到的是宋长玉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为了逃避矿难的责任。就如鲁迅在《娜拉走后会怎样?》
中所说的那样: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宋长玉也是如此。